丹青不知老将至
家乡区县: 信阳市固始县
丹青不知老将至,蹉跎岁月,已届耄耋,未尝有成。这是画家凌晨的感言。凌晨,就是后半夜至天亮前。这个名字怎么来的,这得从老人80多年的绘画经历,及许多人生故事说起。先从史老对凌老“马”的评价谈起。
一、2001.8 一幅《八骏图》受到史树青先生赞赏。
史树青(1922-2007)国家近现代书画鉴定委员会副主任。这事得从1991年说起,当时舟山骨伤医院院长顾鹤鸣先生邀凌老前往舟山普陀旅游。为表示谢意,同时也表达对改革开放后祖国日新月异大好形势的抒发,特意画了幅《八骏图》赠给顾院长。
时隔10年,2001年8月1日舟山观海堂冯经理为了鉴定自己收藏的几幅名家作品真伪,专门去北京邀请史树青先生来舟山。史老很快就鉴定完几幅作品,冯经理觉得机会难得,就打电话给顾院长,让他将收藏的书画作品也拿来鉴赏一下。没想到顾院长将凌老的《八骏图》也带上了。更没想到史老一看见《八骏图》颇为赞赏。提笔在画上题句云:“胡马大宛名,峰棱秀骨成。竹披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生死。凌君写八骏,万里驰纵横。略改杜甫诗句奉题先生《八骏图》。悲鸿先生见之,当为首肯。”这样的赞誉始料不及。之后,冯、顾先生商量打电话,邀凌老再到舟山。凌老去后才得知受到史老赞赏,颇感意外。
二、四、五岁时喜欢画画,裱画店老板要卖我画
凌晨,原名凌公望,1923年10月生于大别山麓。下面是凌老自述:我的祖上没有从事绘画的人才。母亲是中学教师,是当时不多的知识女性,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和兴趣培养。1931年,我八岁,就读于河南开封省立第五小学,是省模范小学,师资很好,教美术的老师是美术专科学校毕业的,叫李明轩。美术兴趣就是这位老师启蒙的。那时没有条件学油画,油画颜料是进口的,价格高,买不起,只好学国画。国画一学上手,就特别喜欢,悟性也特别的好,画的画总在全校拿第一。有了成绩,更激起了画画的兴趣,一有空,别的同学玩去了,我就画画,对我来讲,画画就是玩,久而久之,我对画画达到痴迷的程度,被大人叫做“画迷”。
小学毕业,初中读了半年,发生“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战爆发,全家从开封逃回老家。姐夫在县里办了个小学,看中我的美术特长,聘我当美术老师。真有意思,自己还是小孩,却当了老师,这也算是稀奇事吧。当了半年老师,便继续读初中。空时我自娱自乐,画了一幅荷花,一幅老虎戏孔雀,老虎跳起去抓孔雀的尾巴,完全是自己想象的。孔雀是鸟中之王,老虎是兽中之王,既吉祥又祛邪。我拿去装裱,裱好后,店老板把画挂出来,有人看见后,称赞不已,一定要买这两幅作品。我去取画,店老板问我卖不卖,我说我是小孩子,怎么能卖画呢。那人怕我不肯卖,出了一个不错的价钱:一担米(相当于300斤米)换一幅画。那时,这个价很有诱惑力,但我还是不卖,倒不是嫌价低,而是不敢卖,买卖应该是大人的事。在店老板的再三劝说下,我只好同意了。
那是抗战时期,老家没有高中,我只能到安徽六安读高中,从老家到学校要走200多里,很辛苦。有次我画幅老虎,被美术老师看见,很是喜欢,要了去挂在自己宿舍,老师的朋友看见,连连称好。我在虎图上没有题自己的名字,他们以为是老师画的,老师也没有说破,再说告诉他们是一个学生画的,他们也不会相信。于是拿些纸向老师索画,这为难了老师,老师根本画不出来,只好请我画。我呢,拿人家的纸练画,何乐不为。给老师代画,既是练画又给老师挣足面子。我的作品无意中得到认可,更奠定我对于绘画艺术孜孜以求的信心。
三、1946年考美院考得第一名。大画家临我小字辈的画。
为了进一步深造,考国立艺专是我梦寐以求的。1946.9抗战胜利后,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从重庆迁回杭州,进行战后第一次招生。赴考很辛苦,因当时没有交通工具。步行到蚌埠坐火车,到杭州整整走了一个星期。到杭后,我傻眼了,参加考试的都是上海、苏州美专的毕业生,还有许多画家的后代,况且杭州本是美术之乡,可谓强手如林。我想这下完了,肯定考不中,但既然千里迢迢来了,就只能硬着头皮试一试。考国画是潘天寿大师监考,他看了我的作品,笑了笑,不作声。我心里直打鼓。发榜要一个星期,住不起旅店,就恳请老师在教室将就一下(自己带有被子)。到了发榜的日子,我从教室往大门屏风走,心情很忐忑,因太想考中,急于看结果,又怕看结果,我伸过头看见前排第一个字“凌”,仔细看是我的名字,我居然考第一名,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取得前二名可享受公费待遇,从此我读艺专学费、吃住全免费。那时的校长是潘天寿,教授是黄宾江、郑午昌。有这些名画家点拨,再加上系统的学习,我艺术水平日臻提高。
1948年底,北京和平解放,末代皇帝溥仪的堂兄溥儒,是与张大千齐名的画家,他不了解共产党政策,生怕杀头,从北京逃到杭州。我听说后登门求教。我带一幅松鼠,一幅锦葵,并另准备了两张白纸,请溥先生在我的两幅画上题字评论。另写一幅字,画一幅画。溥先生很随和,慨然应允,叫我一个星期后来拿。七天后我去溥先生家,溥先生从书架上取下一卷画,从中抽出我的四幅,这时我惊奇地发现,还有两幅和我一模一样的“松鼠”和“锦葵”。显然他是临我的画。我回来的路上纳闷,一个大牌名画家,怎会临我小字辈,现在想想才明白,这是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才是大名家。
四、解放后,业余创作了一批作品。1957年反右时,无意中救了李震坚。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6月毕业后,在谭震林书记领导的省委农村工作团搞土改。后进浙江工人日报社任美编。这期间经常给工人上美术课,培养工人画技,有两名青年工人经我推荐,读美院深造,后来学有所成。刚解放时,中国美协主席江丰提出国画不科学,取消国画,我转而学搞版画。那时我年青、精力充沛,常常搞创作工作到后半夜。创作了一批作品,如铜版画《转运》参加1956年第2届全国版画展和中国现代版画展到欧亚美等11个国家展出。刊载于《人民日报》《文艺月报》,并作为国礼赠送给11个国家美术馆收藏。木刻《转移》体现了金萧支队在四明山打游击时的军民鱼水情。参加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纪念美展。刊载在1957年《美术》、《解放军画报》。并被军事博物馆收藏。这期间,我常用笔名:凌晨投稿,久而久之就成了现在的名字了。
李震坚(1922.5-1992.10)擅长中国画,是现代人物画的领军人,培养了一批优秀人物画家,如周昌谷、方增先、刘文西等(人民币毛主席画像就是刘文西画的)。那是1957年秋季,正是整风反右斗争最激烈的时期。李震坚被批斗而一时想不开。欲寻短见。一个星期六的傍晚,饭后无事,想和同学李震坚聊天。于是来到孤山边的国立艺专教师楼。推开震坚虚掩的门,见他昏睡在床上,我叫他几声,推几下没有反应,觉得不对头。再一看桌上有安眠药瓶,觉得要出人命,马上到外面求援,时逢周末,找不到人,我赶紧跑到平湖秋月叫了一辆三轮车,和车夫把震坚抬上车,迅速拉到杭州市一医院,医生一查病人已经休克,再迟来要出人命的,立即进行抢救,一直到后半夜才稍有好转,当时没有特效药,只打了一针吗啡,医生说只有大量喝浓茶,我就去张罗煮茶给他喝,这样天亮后见他慢慢苏醒。这是一次独特的经历,至今记忆犹新。
五、1962年,由于有家庭成份和海 外关系等因素,被下放农村20年。下放时,把我当右派。落实政策时,不把我当右派。
1962年,我在没有任何错误的情况下,被无辜下放河南农村,作为改造对象,强行参加农业劳动。我是一个读书人,没干过体力活,全家七口人,就我一个劳动,那个苦可想而知。不仅如此,因是地主成份,孩子读中学的权利也剥夺了,十四、五岁就参加农业劳动。我问,我不是右派,干嘛如此对待我?他们反问我,你不是右派,干嘛下放这里来。再说,你出身地主,弟弟在台湾,不是右派,起码也是美蒋特务。1966年,红卫兵抄我家,仅有的家当,包括我收藏的古画,如唐伯虎、吴镇、郑午昌、吴昌硕,溥儒等名家作品,还有老师潘天寿、黄宾虹的画作,全部抄没一空,收据也没有给。(1981年平反后我去追讨,发现有几幅古画在当年的红卫兵手里,但苦于没有证据,讨不回来)。那时被害的全家简直无法活,当然更没法画画,只是偶尔在县里画画毛主席像。这样的折腾,我对绘画失去了信心,不希望后代再学画了。那时我40多岁,正是创作的黄金年龄,被严重的耽误了二十年。二十年,一生有几个二十年,耽误不起呀。
1980年党中央拨乱反正,我回到原单位要求落实政策、安排工作。人家说,你不是右派,怎么落实政策?幸亏遇到了一位大恩人,他是省总工会主席赵景堂。当年我们两家同住一个院子,关系很好。他说,老凌呀,你这个人一辈子不会犯错误。他帮我联系相关部门,解决全家户口问题。使我享受离休待遇,我实在太感谢赵主席了。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开了第二次艺术生命之花。凌老为把失去的光阴追回来,以百倍的热情创作了一批中国画,如:《老山兰》、《墨牡丹》、《野火烧不尽》等均获大奖,并得到一致好评。又被批准成为了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1988年参加“纪念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全国书画展,荣获一等奖。2006年9月参加加拿大温哥华举办的天骧杯中国画马艺术大展获天骧奖。尤其受到史树青先生的高度赞誉——“大作画马诸图形神兼备,确有悲鸿先生未到之处”。近年被聘为世界教科文卫组织首席艺术家,中国国家书画院副院长,台北故宫书画院名誉院长。九十高龄的凌老,仍在思索创新,探求艺术新的造诣,享受绘画中的乐趣,他说“活到老,学到老”
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就送梧桐子“ ”支持吧!
”支持吧!
已获得0个“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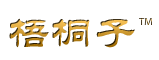
 河南省孟州市
河南省孟州市 山东省新泰市
山东省新泰市 广州市海珠区
广州市海珠区 安阳市 北关区
安阳市 北关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