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里的外公
家乡区县: 临沂市罗庄区
我完全不记得我的外公。他的样子,他的声音,他有没有胡子,我都不记得。 关于外公的一切,我都是从母亲或外婆或其他年长的家人那里听说,像听一个故事那样。我依着故事里的主人公,在记忆的空白里一点一点勾勒出外公的音容笑貌。他们说他高大魁梧,有接近一米九那么高;他们说他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后辈里只有三姨和我遗传到这眼睛的漂亮模样;他们还说他性格温和,从来不发脾气,即使外婆在小小的草房子里闹翻了天,他也一笑了之。
外公是一个勤劳的农民,他还是一个赤脚老中医。他摆在家里那些瓶瓶罐罐的中药,大多都是自己进山采摘而来。他酷爱背上几日的干粮和水,穿一双轻便的鞋,徒步近百公里寻到那些连绵起伏的山,他一个人爬山,一个人攀崖,一个人采药,一个人露宿山野……真不知他哪里有那么多胆魄和面对孤独的勇气。
总是要等三五天后,外公蓬头垢面、风尘仆仆地归来,背袋里满满的草药代替了干粮和水,身上的衣物也都脏兮兮甚至划破了许多口子。外婆看到这样一个令人担心又貌似疯癫的人,不免是一阵生气和吵骂,可外公却在忙着卸下他的草药,一边认真细致地归类和晾晒,一边对外婆的骂声一笑置之。外公时常用自己的草药医治病人,但大家都是山野村夫,穷得叮当响,于是外公只管治病救人,治好病的人有钱的给几个钱,没钱的给些东西就抵了,实在是不愿给钱或穷得揭不开锅的,也便作罢了。为这赔本的行医方式,外婆也是要经常生气和吵骂的。
在我很小的时候,是跟着母亲和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的。高大的外公时常怀里抱着个小小的我,逗我开心,和我说话。等我再大一点的时候,外公就时常把我扛在他宽阔厚实的肩膀上,一副自豪和骄傲的样子,带着我溜大街赶大集,买各种好吃的给我,买各种好玩的给我。他毫不吝啬地疼爱我。
有一年冬天下着很大的雪,三岁的我却吵着不吃饭,哭喊着只想吃芋头。家里是没有芋头的,母亲和外婆只想等我闹够了就好了,可外公却已披上一件厚厚的破棉衣,推门走进正在飞扬的雪里。他一边走一边回头说:“今天是马庄集,兴许有人出摊,兴许就有人卖芋头呢。让丫头别哭,等我回来。”
马庄很远,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风雪里,走了很长时间才赶到马庄平时逢集出摊的街道上,如他心里隐隐担心的那样,因为大雪,集上一个人也没有。他毫不犹豫转身往回走,他的心里还有另一个办法。等外公回到自己村庄的时候,天色已经渐暗了,他没有停歇,开始在村里比较相熟的人家门前挨家挨户地敲门,询问有没有芋头。他敲了好几家,终于有一家回答说:“有!”
但时值隆冬,芋头是和地瓜一起窖在地窖里的,如果在飞雪漫天里打开地窖,很可能使地窖里的食物都烂掉。同村人有些不愿意,外公看在眼里,便只能放下一个60岁老人该有的样子,像个孩子一样地在人家面前软磨硬泡。天黑的时候,外公怀揣着从地窖深处取来的芋头,踏着没脚的积雪欣喜而归。
就在冰雪消融初春将近的一个夜晚,外公起身入厕,却一头栽倒在地。等家人发现的时候,外公已经躺在院角通往茅房的小道上奄奄一息,他让母亲抱我在他身边,用虚弱的声音向母亲一遍一遍地嘱咐:“这丫头没爹,你要好好待她,好好疼她啊……”这是他生前最后的话。
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就送梧桐子“ ”支持吧!
”支持吧!
已获得0个“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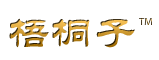
 河南省孟州市
河南省孟州市 山东省新泰市
山东省新泰市 广州市海珠区
广州市海珠区 安阳市 北关区
安阳市 北关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