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村庄
家乡区县: 达州市通川区
老房子很旧,是那种青砖青瓦的低矮瓦屋。父亲说那年头可算很长脸了,而现在父亲已年且半百,青丝微霜。姐姐嫁了人家,哥哥也早已完婚,父母辗转外地打工。一切都变了,无法复原。人世变幻无常,唯一坚守不变的,也许只有老宅,那座老房子了吧。
暑假归来时荒草疯长已蔓延整个院子;楹联早退色剥落,孤零零地挂在门上;蜘丝无情地缠绕了每一个角落,结成了大团的绒花,用火一烧,"嘶"的一声燃成了灰烬,于是熄灭,跌落,再无人问津。没有人在乎蜘蛛从此是否无家可归。
我把自己关在老宅里随心所欲地懒散,日复一日。每天坐在树阴下面对着离离荒草发呆,脑海中一片空白。难看的壁虎摇着尾巴在墙上悄无声息地爬来爬去;老鼠从脚边箭一般窜过,冲进高高的荒草中,发出窣窣的声响;黄昏时分,成群结队的大脑袋蜻蜓就在我头顶上盘旋,让我想起儿时唱烂的歌谣:"光光蜓,来吃麦,一把扫帚捂一百。"
在我们那儿的方言中,"蜻蜓"是叫"光光蜓"的。我从未问过大人为什么,只是这样叫着。如果你说"蜻蜓",别人是要看不起你,讽刺你"拽"的。
夕阳西斜时,我会搬着凳子在门口的树林中看书。一束束阳光斜着穿过碧绿的树林落在地上,杨树的影子被拉得细长。一位走路颤颤巍巍的干瘦婆子抱着一捆青草,拉扯着一大帮灰不溜秋的白羊,见我在读书,就问我啥时候开学,咧开嘴笑着,露出一嘴褐黄而又参差不齐的牙。血红的夕阳映出她的轮廓,蓬松的白发支棱八叉地缠在头上。
那个暑假我一直用那台笨大陈旧的老式收录机收听着音乐节目,咿咿呀呀净是些缱绻悱恻的情歌。长乐飘飘,有时我会像邻居老汉那样在闷热的午后,躺在凉席上伴着电台情歌睡去。而醒来时,我总是把手搭在旋钮上不停地找台,并把音量调到足够大。否则的话,我就会听到屋后华意那个大喇叭里传来《公母瘸子谈恋爱》或《二流子卖媳妇》中女人扯破嗓子的尖唱。明明是更年期女人,却硬是涂脂抹粉攒个发髻,裹上旧衣服装扮成花甲老人状,可仍扭动着弱不经风的身子,捏着**浪调卖弄风骚。
华意已年逾而立,却没有成家。也不知因为得了什么痼疾而变成了瘸子,成天驾着一个沉重的板凳"咯噔咯噔"地东走西跑。每天他大喇叭里播放的柳琴戏或"妹妹大全"吵得我头昏脑胀。而村里的人却是爱听的:须发灰白的老者拄着拐杖,孩子们光着上身,全都鸟儿一样伸着头聚精会神地听那个扭捏的女人唱:"浪不浪,那个看走相;臊不臊,那个看裤腰,哎,那个看裤腰……"并不失时机地会心一笑。华意坐在床上见有年轻的妇女抱着孩子站在门口听戏,就睁圆了蓬头垢面中的一双大眼睛,直怔怔地盯着。口水从宽广污秽地嘴里拉成一线天滴在锅底似的手背上,再辗转他处,他也浑然不觉。
那天华意地大喇叭唱得特欢实,一整天嗷嗷直叫不停歇。因为鱼贩子的三儿子要结婚了。于贩子的三儿子娶的是本村的姑娘玲玲。一天夜晚,两人"不约而同"地不见了,不久之后,她依偎着他笑容甜蜜地回来了。人们在背后纷纷啧叹:"哼,人小心大着呢!"然而鱼贩子照样下了聘礼,张罗起了婚事。结婚那天,我看见16岁的新娘浓妆艳抹,成熟而矜持。在新郎的红伞下,被众人簇拥着面无表情地走入新房,婚纱在阳光下亮得刺眼。我们那儿的风俗是凡是新媳妇嫁过来总要"乱"的,说是吉祥。由于玲玲辈勉且是自家村人,人们就没动手,在嘀哇嘀哇的唢呐声与噼里啪啦鞭炮声中,站在远处一边擦汗一边眼巴巴地观望。
玲玲的奶奶老顾就十分得意,逢人就说可不能像从前那样叫她了因为她又长了一辈。因为论辈分,玲玲是该叫新郎叔的。老顾是一个骨骼健壮的老女人,整日在田里蹶拱蹶拱地打药施肥薅草浇水。如果有人掰了她的玉米或撅了她的花生,她就会掖着庄稼秧子溜着大路祖宗八代骂翻半个村子。直到嘴角堆满了白色的泡沫满脸涨红,还在跳着叫骂。孩子们是很在背后戳她的。对于她长辈分的说活,人们虽不以为然但却碍着颜面不便冒犯,背下里却深以为耻,有些男人就说:"长什么辈分,她孙女又没嫁给我?"
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就送梧桐子“ ”支持吧!
”支持吧!
已获得0个“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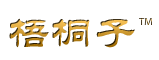
 河南省孟州市
河南省孟州市 山东省新泰市
山东省新泰市 广州市海珠区
广州市海珠区 安阳市 北关区
安阳市 北关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