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村庄(2)
家乡区县: 达州市通川区
鱼贩子的三儿子结婚后,村里年轻小伙子间就流行起了黄品源的《小薇》。因为鱼贩子的三儿子买了一盘城市里早已淘汰,而农村里却如凤毛麟角的"流行旋风"。停电的晚上,三五成群的小伙子聚集来在村里的大路上游手好闲地晃荡,并且随时都可能听到哪一个光着膀子的青年放开嗓子吼出从不在调上走的歌儿:"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她的名字叫做小薇……"有时巧遇远处散步的姑娘,就会吹起响亮的口哨,一人模仿张卫健高唱:"大姑娘,大姑娘我爱你哎……"然后众人附和:"哎哎哎哎……"响起一阵粗犷的笑声。于是她们便会骂着回避。
听着这样的声音,日子一天天流逝。天气也越来越闷,空气中仿佛飘满了窒人的粘液,让人无所适从。老人们摇着残旧的蒲扇望着灰蒙蒙的天空,感叹说总要下场雨了吧。终于,那阵扬起几丈飞尘的狂风之后,滚滚的浓云将下午变成了漆黑的夜晚。人们连滚带爬地奔向家去。一道巨大明亮的蓝紫色闪电划过漆黑的天空,然后"咔嚓"一声响雷劈天坼地,硕大的雨点随即"啪啪"直砸下来。
大雨一下就滂沱了好几天,我就蜗居局促一宅之内。望着小小的村庄迷朦在茫茫雨雾之中,大风不断地冰凉的雨水潲进屋里。雷辊电霍,络绎不绝。我担心村子在这样风雨飘摇中会不会被摧残地面目全非灰飞烟灭。这样想着,窗外淫雨霏霏,于是一种惆怅随着细雨轻轻飘扬了起来。
大雨过后,人们便绘声绘色盛传神龙又要劈死哪个不孝的小舅子了,证据是村南大杨树干上"被龙爪抓破的树皮"。人们的语气坚定得不容置疑,仿佛被劈的是自己一样。可农忙起来,那些荒诞不经的谣传便如风雨中的落花,不知被打到哪里去了。偶尔被阴天套被子的妇女絮絮叨叨地提起,打发无聊的时光。
云开放晴之后,骄阳似火,气温也节节攀升。于是常见一群群男人脱光衣服,在烈日下跳入蓝蓝的河水中,笑声朗朗。身着入时的少女顶着红色的小阳伞提着裙摆在田间薅草,哼着《粉红色的回忆》或《我只在乎你》--跟不上时代的歌谣。日子过得没有生机,太阳每天东升西落炙烤大地。睡去醒来时,只见半壁残阳昏暗,好似照着一段落灰的旧时光。墙上干枯的牵牛花叶在微风中左右摆动。二层小楼虽明亮别致,在将逝的斜晖中,却掩饰不住落伍的陈旧。空气静止。残阳如血。如出一辙。
天气炙热难耐,在由于要供应城市电力而停电的时候,人们便潮水一样涌向南地的坝子乘凉。所谓坝子,就是一座低洼的土桥,两边各置一排水泥管子通水。每逢连日暴雨河水涨满之际,凶猛的水流便会将坝子的一部分冲塌陷。大水退去之后,人们再用架车一车一车地拉土填平,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了。也曾有人筹划要修一座像模像样的石桥,但村里有人不愿掏很少的建桥费,就这样拖着,渐渐也就不了了之了。洪水泛滥的年头坝子仍被冲塌,人们仍骑着自行车路过坑坑洼洼的坝子去赶集,人们仍说着它的不方便,可坝子终究是没有改变。
乘凉的人多得是妇女和儿童,所进行的活动主要是打扑克。铺一张席子或化肥袋子,脱掉鞋子垫在屁股下面坐着,便气势汹汹地玩起了"打八十"或"斗地主"。也有肥硕的妇人撩起宽大的衣襟给嗷嗷待哺的婴儿喂奶,不知谁家的狗摇着尾巴在人群中往来穿梭,瘦得猴子似的儿童钻进水泥管子里戏水,偶尔还能捉到一两只活崩乱跳的大虾,便扬着手里的胜利品向人们炫耀。
结婚不到一年的媳妇靓装丽服手执一罗扇款款走来,却并不坐下,而是捏着矜持的劲儿斜倚在树边。轻轻摇着扇子与旁边抱着孩子的妇女有一句没一句地搭讪。渐渐扯到领孩子的问题上,抱着孩子的妇女义愤填膺:"不自己领谁给你领?指望那个臊老妈子?门也没有!成天往家里拾腾东西,一点东西都跟小孩子挣。上次蒸洋槐花,憨老妈子竟用麦麸子掺,啊哈哈--呦,二狗又尿妈妈身上了。--地里的草长荒了,可得薅!唉,累死累活的谁看你一眼。谁叫咱男人没本事投胎成省委书记呢?唉……"?
新媳妇仿佛很同情,感同身受地说:"谁又不是呢?……"
妇女打断了她的话:"你好多来!"
"俺好啥唉?"
抱孩子的妇女冷笑道:"好啥?起码你老公公老婆婆能出门打工挣钱,孬好能给点。像俺这样老公公死了老婆婆又憨不愣腾的,谁给你一个子儿?"
新媳妇也感慨万千:"人家儿女一大家子,哪里顾得了你!有钱了也得给人家小儿子娶媳妇,哪里轮得到俺?"
"等你有儿子了,一家人疼得宝贝蛋似的,谁不依你呀! 你还有个小姑子,又有人领孩子,好多来!"
闻此语,新婚的媳妇便作害羞状,只是低着头,轻摇罗扇,不答话。
在闲谈与打扑克声中,热辣辣的骄阳不知不觉漫过了树梢,将树和人的影子扔在东面灼热的地上。人们陆续拎着席子或拍着麻木的腿离开了,不多会,热热闹闹的坝子就变得冷清而寂寥。我坐在坝子边缘,聆听脚下潺潺的水声。望着河流蜿蜒绵绵伸向远方,我能愣愣地发呆半天。知了在树上鸣叫,却犹如近在耳畔,聒噪个无休无止。阳光普照,小小的村落却充溢着森森的阴气,混合着庄稼与草木的腐烂气息,纠缠撕扯,再也分不清。投出去的石子在河中心荡起一层层的涟漪,水波起伏荡漾向四周扩散。石子在表层清冽的水中悠悠下沉,渐渐深了,深了,下沉,就再也看不见了。
站起来时,夕阳已血红卧野。望着苍茫的田野,感叹只是日暮乡关。一年又一年,夕阳都始终如一,映照着沧桑变幻的大地。纷纭的生命自生自灭,其间的自然与生机,卑琐与猥劣,也许我们谁也说不清。
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就送梧桐子“ ”支持吧!
”支持吧!
已获得0个“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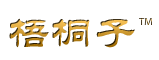
 河南省孟州市
河南省孟州市 山东省新泰市
山东省新泰市 广州市海珠区
广州市海珠区 安阳市 北关区
安阳市 北关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