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洋槐花(1)
家乡区县: 达州市通川区
南国的四月,校园里又飘起了洋槐花幽幽的香气,晚风中行走在婆娑的树影下,不禁又想起了故乡的洋槐花。
家乡是一片坦荡的平原,到处是成片成片的庄稼,在庄稼与庄稼的间歇处,如麻子缀脸,散落着一个又一个的村子。所有的村子,也都那么普通,一排一排的房子,几条横穿竖梭,而又坑坑洼洼的小路,承载着几百几千人,活一辈子。每一家人,分得几亩地,劳动耕作,拉扯几头牲口,喂几只鸡鸭,栽几棵树,日子慢慢过着,一代,又一代,都这样,熙熙攘攘总有那么一群在。然而,隐秘的变换却总是逃过了我们的双眼。那一群人中,孙子早就成了爷爷,而爷爷早已在哭声中入土为安。人世的转换,岁月的更替,现在的一群就再也不是往日的那一群了。离家漂泊的游子经年不归,村子就开始变得陌生了:田地里新添的坟塚宣告了老人的离去,孩子的笑脸在眼前晃动,而于他却显得格外生分了。唯有那石墙青瓦的房子不倒,河畔高树细枝长存,才能给游子以安慰,证明那风物依旧,并非他乡。
平原上的树木种类贫乏,但道路两旁,却随处可见杨楝之类,梧柳之属,在夏日的蝉鸣中蓊蓊郁郁。每逢冬去春来,新鲜的生命便如锅中之水般沸腾了开来。且不必说那蔓延四溢的野花,墨绿广阔随风翻滚的麦浪,还有那唧唧喳喳乱窜觅食的雏鸡,单单是树木新抽的嫩叶散发的幽香,陶醉其中,也足够心旷神怡。立春之后,村子内外随处可见春风的痕迹,清泠泠流动的河水,远现近却无的草色。然而树枝仍是光秃秃,乱蓬蓬的一团,繁茂喧腾的春天却总是姗姗来迟。可是,不知道哪一天早上醒来,睡眼朦胧中,你会听到淅淅沥沥的春雨未停,而微风潲一二雨丝入窗,清清凉凉,吹面不寒。睁开眼睛,世界就一片明晃晃的翠绿了。一簇簇肥大新鲜的树叶挂在枝头晃动,黄如透玉,绿似凝脂,欢欢喜喜挤作一团。树叶相击,飒飒作响。雨水划过嫩叶,纷纷扬扬地随风飘洒下来,亲在脸上,落在肩头,也无须拂拭。然而扬花蒙蒙,乱扑人面的情景易衰,待到树叶树叶如妙龄的姑娘,呼啦啦长开时,满树臃肿,便只见威武,不见雅致了。
故乡风树,新旧相续。酥润的春雨刚晕开了娇嫩可人的杨叶,四月的风中就飘起了洋槐花的清香。故乡随处可见洋槐花树,屋前庭后,村南庄北,烂漫时节,景随步移,那一蓬蓬,一簇簇,花开无主,都在你眼前轻摇。一树一树,都挂满素雅玲珑的花串。相形之下,那鳞状般的叶子便微不足道了。每当此时,整个村子都沉浸在了芳香的怀抱中,所到之处,香气扑鼻,清心怡神,仿佛每一寸皮肤上都布满了嗅觉器官。而如果恰逢月半,晚风习习,天朗气清,肥硕的月亮高悬长空,光华流泻,打在树梢,一片明晃晃的银亮匝地,摇曳不定。徜徉在明明灭灭的林间,幽香氤氲,伸展双臂,让晚风抚过肘腋,而灯火阑珊,人声渐远,抚摸着粗犷的树皮,心中常常会涌起种种美好的忧伤,无可名状,却又那么实实在在。以至于岁月流逝,多年以后回想那些恍惚的过往,记忆中的少年仍然沉醉忘归,昨日的感伤如初,依旧激荡着今天的心怀。
然而花红易衰,一旦暖香袭人,我们便迫不及待地够下洋槐花了。洋槐花树多刺,攀爬而上是不大方便的,高效而廉价的工具是爬钩。寻一根粗细适中,长度足够的棍子或竹竿,再找一把镰刀,用绳子绑在棍子或竹竿前端,系稳扎牢,便大功告成了。奶奶健在时,每年的爬钩都是她弄的。那时我还小,经常跟着奶奶,携着爬钩提着篮子去村头放羊。把羊拴在树上,任它去吃左右的青草,我们就用爬钩去削挂满花串的树枝。细小的枝条好削,锋利的镰刀划过,就干干脆脆地荡落而下。但粗大的树枝却不是那么容易屈服了,通常都需要使出很大的力气,拖着爬钩努力向后下方拽去,那树枝弯得如一张弓,你只要不松懈,继续用力,听到“咔嚓”一声,树枝就断了。而枝之粘韧者却是十分的难缠,削也削不断,拉也拉不折,几支残损的花束在上面,图然碎落满地花瓣。
洋槐花枝削下来之后,我们就要赶紧拉到一旁,捋起花朵,不然,羔羊的嘴巴是不会闲着的。花序井然,从头到尾一捋,便只剩下一根青绿的嫰梗了。美丽的花朵鱼跳珠溅般落下,须臾慢慢的一篮便在了。剩下的枝叶委顿于地,也就任羊羔们大快朵颐。将近晌午,艳阳高照,着满蓝洋槐花,赶着肚子滚圆的羊群归来,咩咩的叫声都格外的悦耳。
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就送梧桐子“ ”支持吧!
”支持吧!
已获得0个“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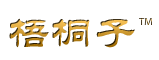
 河南省孟州市
河南省孟州市 山东省新泰市
山东省新泰市 广州市海珠区
广州市海珠区 安阳市 北关区
安阳市 北关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