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风物记之银金树
家乡区县: 韶关市南雄市
我最难忘怀的,是我家后院里那一棵苍劲葱郁的银金树。那一树如盖的绿荫,一树深邃的云天,恰似那闪烁的星辰,梦幻的丽眼,萦萦绕绕不散于我记忆的心空……
我的故乡在粤北山区,自然山多树也多。山是苍苍茫茫的山,树是密密麻麻的树。其他不说,仅是我的村子赵屋,山前山后皆是树。那些树苍劲粗壮,高大挺拔,恐怕已历经了百年沧桑,稍微年轻的也有数十年风雨。在我们村子通往外面的一条公路边,便生长有枫树、樟树、荷树及一些我至今不知名的树。它们的桠枝硕大无比,个别的早已枯败只剩下光溜溜的、黝黑的或满目苍痍的树丫,乍一看皆触目惊心直指苍穹。但大多数的树枝仍是那样生机蓬勃,一年四季一片青葱翠绿抑或橙黄灿烂。无论枫树、樟树还是什么树,它们总是静默地沐浴着阳光,有时也在风雨中摇曳生姿。它们感应天时地利,经受岁月风尘,俨然一个个慈眉善目的长者,忠贞不渝地守护着我的故乡,荫护着每一个来往于它底下的我的乡人。
地院的那棵银金树也不例外。它苍劲挺拔、高大粗壮。在我童年的印象中,它似乎永远那样茂盛葱郁。风轻云淡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它满树的绿叶稀稀疏疏地筛落下斑斑点点的阳光,这儿或那儿,又经微风的吹拂,幻化成精灵古怪的光影满地院里欢呼雀跃,不由得引得我们在银金树下一个劲儿地追跑;下雨了,我们躲在银金树下,起初只听见一树窸窸窣窣的声音,却很难见到一两滴雨水溅落在我们的身上。这样的时候,我们常可气定神闲凝望着一旁池塘中泛起的一个个涟漪,看着它神奇地荡漾开去随即又幻灭于无影无踪的世界。除非倾盆大雨,否则我们不会回去。只要云过雨散,我们又在树底下嘻嘻哈哈打闹不已。银金树,风雨过后它也微笑着,仍然张开它那宽厚而又温暖的臂弯,深情地怀揽我们,一任我们尽情挥霍童年快乐的时光。
到了五六月间,银金树又会结出一种圆形的果实,绿绿的。这时我们便砍来竹子削成一截长长的竹筒,另用一根筷子合做成一把竹枪,而子弹就是银金树的果实。我们用这种竹枪来击射对方。这也是童年最为开心的一种游戏。为了这开心的游戏,我们必须先从银金树上获取“子弹”。于是,我们能爬树的爬树摘取,不能爬树的则从家中找来一根长木,上面扎上一把镰刀,站在树底用它来割下结有串串果实的银金树的树枝。也有举起一根长长的竹篙胡乱敲打的。通常几竹篙过去,树上便骤如暴雨倾盆,银金树的果实纷纷满地坠落。见此情状,我们个个犹如猛虎下山,以最快的速度去争抢果实。自然其中又别有一番热烈的轰动。
为了几根树枝数颗果实,人人你抢我夺,甚至滚来爬去不惜相互扭打成团,然而,到了最后我们往往又能顾及那些连一颗“子弹”都没有的同伴,多少分点给他,好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到这游戏的乐趣。银金树,尽管我们任性地攀折它,弄伤它的枝叶,可它还是那样地包容,那样地善解人意,总是一脸温和地默默注视着我们。至今思来,我内心仍会泛起些许情感的波澜,胸中常有融融的一片暖流……
可是,就是这样好的一棵银金树,后来?居然被连根挖起,倒了,也永远消失了。而后院也不再是后院,就在原先我们一直认为空旷而又快活的乐园的地方,矗立起了一排排高矮不一参差不齐的楼房,显得狭窄而又沉闷。想想世事的变迁也恍若梦幻,记得我家原来还处在村子前沿的位置,放眼望去村前的原野,远处的山峦,以及蓝天白云朝霞暮霭尽收眼底,视野相当开阔。但似乎经年不久,我家前方却层楼叠嶂,如迷雾蔽日,不但视野受阻天光也日渐黯淡下去——实际上,我家早成了村子的中央。因为,那些不断萎缩的田野里,又已为更多乡人的新居所盘踞。此故乡非彼故乡。可怜的又岂仅是那一棵银金树?
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就送梧桐子“ ”支持吧!
”支持吧!
已获得0个“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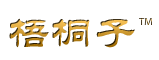
 河南省孟州市
河南省孟州市 山东省新泰市
山东省新泰市 广州市海珠区
广州市海珠区 安阳市 北关区
安阳市 北关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