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那些事
家乡区县: 济南市商河县
鼓子秧歌的流传赖于祭祀活动
“祭祀”和“礼俗”是统治阶级约束人民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手段。殷商以前,人们以目神为万物主宰,朝夕祭之。周代则以天帝为尊,节气(日)受祭,并和神农、后稷并而祭之,一直延续到清末。典仪非常隆重,上至天子、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下至州府县衙,上下一齐搞,最初带有强制性和半强制性,后来逐渐变为习惯。《商河县志》记载的县城郊祭活动:立春前一日,官府率士民具芒神土牛,里人行户扮渔读耕樵诸戏,在日出前出东门,朝东南方向顶礼膜拜,日出时看太阳光芒能预知当丰农事好坏。上述可以看出,当政者需要通过“祭祀”、“以驭其民”,芸芸众生也趋于对命运的困惑,企盼神祖赐予幸福。农村的“礼俗”,则由族长率“渔读耕樵诸戏”,正月初七(人日)晚上到寺庙祠堂祭神拜祖,烧香包跑“行程”,庄严肃穆,献上三牲、三经,三拜九叩,烧柴禾烧纸钱跑“场子”,祈祷六个方面的要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多子多福,福禄吉祥,消除兵祸,远避罪疾。
由于“渔读耕樵诸戏”(现在称鼓子秧歌),常年参加“祭祀”、“礼俗”活动,成为封建社会惯性运转机制的一部分,这种直接的社会功利性,成了民间舞蹈价值取向的一种恒常因素,也就给了鼓子秧歌以生存和流传的条件,因而一代一代传了下来。
鼓子秧歌从实用功利艺术逐渐向自娱性转化
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从外地迁来大批移民,他们不仅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也带来了各地的乐舞文化在商河大汇合,民间歌舞从减轻劳动重负、祭祀驱壤、鼓舞战斗热情的实用功利艺术逐渐向祝福游艺、自我娱乐转化,主调由庆重神秘演化为喜庆欢乐,明清时期兴旺发达。
鼓子秧歌当地俗称“跑(闹)十五”、“闹玩艺儿”,集歌舞杂耍于一场,是汉代“百戏”的延续。民间活动正月初七晚上祭祖,初八正式开始,十七晚上落伞,前后十天,其中十五、十六、十七三天为高潮。《商河县志》记载的城里“跑十五”盛况:“举国纷纷兴若狂,新正十四挂衣裳,明朝但愿无风雪,尽力逞才闹一场”,“是日士女云集,途为之塞,自晨至暮络绎不绝。”“里人行户扮渔读耕樵诸戏,酒筵悦歌竞为欢会,凡三夜”。农村则根据自身条件,将若干种文艺形式综合在一起,重点表演伞鼓舞,舞者不歌,歌者不舞,这种"百戏"形式的自娱性活动,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借用简单的道具,先人传下来的技巧,把压抑的情感,在合情合理合法的时空中,将平时说不出来、不敢说、不能说的话,把窝在心里的酸甜苦辣,一古脑地通过身体各部位的律动,亦舞亦蹈亦说亦唱地宣泄出来,得以心理上的自我调节,自我安慰,自我解脱,重打锣鼓重开张,以期待来年胜今年。
鼓子秧歌的继承发展在当今
商河地处偏僻,交通不便,漫长封闭的自然经济,不仅滞缓了生产的发展,也使民间舞蹈带上浓厚的小农经济色彩,舞蹈技巧(尤其是“头伞”领场子)是父教子、子教孙辈辈相传,组织形式是封建家长制的因袭,它不仅造成鼓子秧歌鲜明的区域性特点,并因裙带关系的局限性,在全县逐渐形成三种伞鼓流派,尽管各种流派相互渗透,形成各具风格的“一个村一个样”,但由于“天不变道亦不变”,虽然千百年流传下来不走样,但“提高”相当缓慢,粗看起来年年都是老一套,并被当政者认为它是民间杂耍不登大雅之堂,任其自生自灭,尤其在日寇入侵的八年里,人民痛苦,秧歌几乎绝迹。1945年商河解放,伴随着发展生产,参军支前,群众性秧歌出现热潮,成了人民获得新生精神风貌的写照。建国后,秧歌活动出现两次高潮,都与党的政策和农民增收的愉悦心情有关,也是文艺工作者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结果。
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就送梧桐子“ ”支持吧!
”支持吧!
已获得0个“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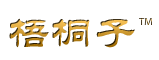
 河南省孟州市
河南省孟州市 山东省新泰市
山东省新泰市 广州市海珠区
广州市海珠区 安阳市 北关区
安阳市 北关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