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指春风
家乡区县: 乌海市海勃湾区
女人不愿拈针线好久了。忽一天满街疯狂的十字绣,女人的包里放着未完成的作品,课堂上慵懒的女生也突然忘情地挑起针线,让我着实一惊。诞生于欧洲宫廷的十字绣堂而皇之步入我们的乡土,我们传统的刺绣哪里去了?
那古典又时尚的丝线,一根根拉来扯去的文化乡愁,如今轮回成各样的形式静息于民间了。抚摸一段刺绣,犹如玩味前朝的诗文与墨香,心不由得细致起来。
古人比今人更好美,懂得美。明代书画家董其昌在《筠清轩秘录》中说道:“宋人之绣,针线细密,用绒止一二丝,用针如发细者,为之设色精妙光彩射目。山水分远近之趣,楼阁待深邃之体,人物具瞻眺生动之情,花鸟极绰约谗唼之态。佳者较画更胜,望之三趣悉备,十指春风,盖至此乎。”好一个“十指春风”,骤然间所有关于刺绣的形容词都失了色。
而中国民间艺术都称刺绣等为女红(gōng),私下觉得若真是“hong”,岂不更美。那种纵深的家族性传承,根深蒂固的女性气息,回味无穷。
幼时看评剧《花为媒》,两个绝色女子洞房互赞,大开眼界,五可夸月娥道:“上身穿着本是红绣衫,踏金边又把云字扣,周围是万字不到头,还有个狮子解带滚绣球……”某处什么花色繁复讲究到极致,穿得还是衣服吗,是披了一身奇葩。
而《红楼梦》里的描写更为惊艳,单是那些名字及色彩之美早把人醉蒙三分。王熙凤一出场“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裉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叫人眼花缭乱。宝玉“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束着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宫绦,外罩石青起花八团倭缎排穗褂”,转身回来又是“银红撒花半旧大袄”,更多了风情。即便粗使丫鬟也“红绫袄青缎掐牙背心”,俱是小巧,天工,绝色。
刺绣是个极细的活。勇晴雯病补雀金裘一章写道:“晴雯先将里子拆开,用茶杯口大的一个竹弓钉牢在背面,再将破口四边用金刀刮的散松松的,然后用针纫了两条,分出经纬,亦如界线之法,先界出地子后,依本衣之纹来回织补。补两针,又看看,织补两针,又端详端详。”是无与伦比的技艺。袭人在宝玉睡榻前刺绣,“白绫红里的兜肚,上面扎着鸳鸯戏莲的花样,红莲绿叶,五色鸳鸯。”宝钗“因又见那活计实在可爱,不由的拿起针来,替他代刺。”可见绣时的心情亦是有传染性的。
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就送梧桐子“ ”支持吧!
”支持吧!
已获得0个“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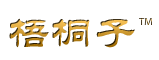
 河南省孟州市
河南省孟州市 山东省新泰市
山东省新泰市 广州市海珠区
广州市海珠区 安阳市 北关区
安阳市 北关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