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 两种心跳
家乡区县: 德阳市旌阳区
坐在沙发上的罗海洛现在还觉得自己额头上的青筋在跳,心中的狂怒与惊诧半天压不住,嘴巴里那股难闻的气味刷了四五次牙仍是难以消去。
“唉……”瞥了一眼室内睡得正香的春袄,罗海洛又回忆起那个惊悚的吻,多年后他会想起这个吻,味道是……酸臭的。
手机突然震动起来,罗海洛揉揉眉心,随后自然扬起罗氏招牌微笑接听:“喂?”
“海……海洛……”话筒传来模糊不清的呢喃声。
又是一个喝醉的女人!罗海洛脸色黑了下来:“筱真梦,我对你已经够仁慈了。”
“海洛……”那边的声音开始哽咽,仿佛如玻璃一样易碎。
“……”
“呜……海洛……你是不会……不会丢下我的对不对,不会放弃我的对不对?”
呜咽愈发大声,女人娇柔的低泣本来应该很容易激起男人的保护欲,可在罗海洛耳里宛如魔音般刺耳。他皱着眉,将话筒拿远了一会才回道:“路我给你铺了,走不走,怎样走在于你自己。”
“海洛你不能这样对我……我们大学就在……”
听到此处罗海洛忍不住嗤了一声,眼底一片薄凉:“你要还念大学的情谊你就不应该那么对程末深,就不该对我耍手段。筱真梦,我罗海洛脾气可没有表面那么好,如果换个人我早就赶尽杀绝了。”好久没有这么耐心地对她说了这么长一串话,他吐了口气,又换回漫不经心的调子,“做好自己的本分。”
对方沉寂了一会,他正不耐准备挂电话,筱真梦突然娇笑道:“罗总真会说笑,怎么在床上不直接拒绝我,现在摆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做给谁看?”声音哪见半分哭意?
“自己送上门来的玩物我有必要拒绝么?”罗海洛仿佛听到什么笑话,眸里依旧一边冷漠,都说罗总儒雅温柔,可他嘴角的弧度加了几分笑意没人知道,“我只是一个正常的男人。”
从容地挂掉电话,罗海洛扯下领带准备再去彻底清洁一下,总觉得还有酸臭味。
黑暗中,春袄慢慢潜回床上,脑子又开始臆想起来,她是个写手,一点蛛丝马迹都可以被她添油加醋地构思成复杂的前因后果。耳朵听着卫生间里传来的流水声,春袄实在有些止不住自己害死猫的好奇心,踮着脚尖小心翼翼地走了过去,拿起放在门外的换洗衣物,忐忑地敲了敲门。
“罗……大少?”
“这么快就醒了?”里面穿来男人低沉慵懒的声音,盘旋在一室湿润的氤氲里,春袄愣神地看着玻璃上倒映出罗海洛模糊的身影,脑子里浮现出自己强吻他的场景,一时觉得窘迫,不知怎么开口。
“咳!傻站在门口干什么?还不把衣服给我递进来。”
“不……不,我不递!”尚还记得自己要干什么的春袄觉得舌头都开始打结了,双颊微微有些发热。孤男寡女,对方就赤裸地站在自己对面,仅仅隔着一扇门。
“不递?”似在琢磨什么,这声音含着戏弄的笑意,“不递我可就这样出来了。”说着,他就转动了门把手。
“唉?别,别!”没想到对方如此大方,春袄反倒更加窘迫了,只得盯着自己的脚问道,“刚刚听到你在跟筱真梦通话?”
“我没必要回答你的问题吧?”罗海洛挑了挑眉,自己还没跟她算账,她倒有时间八卦。
“你……你……你要是不说,我,我就不给你衣服!”艰难地将这句话抖清楚,春袄觉得耗尽了全身的力气。
“程春袄,你也觉得我很好说话是吧?”门的那一面,那微扬的尾音常常带给春袄春风般的和煦,此时却低沉魅惑,带着捉摸不透的危险,如情人的手抚摸过她的耳朵。
“怎……怎么会……”春袄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忍不住往后退了几步。
可惜晚了,门突然被打开,温热的雾气荡漾开来,如触手般缠绕着他的宽肩窄腰和……春袄视线突然僵住。
“好看吗?”罗海洛盈盈笑着,倚在门口。
春袄感觉脸颊烧得厉害,抱着衣物就急速退后。罗海洛饶有兴趣地随着春袄的速度走出浴室,如同天神般,腰背挺直,高大俊逸,压迫着春袄。
“你……你要干什么!”春袄咽了口口水,露出慌张的神色。
罗海洛突然心生一丝玩心,优哉游哉地靠近春袄,直将她逼到沙发背后,双手禁锢住她左右,唇含一丝暧昧不明的笑意:“你说我要干什么?现在可是你在占我便宜。”
头一次这样被男性气息密不透风地包围,春袄绯红了脸蛋,左心房抑制不住地狂跳。和面对程末深的心跳不同,这种心跳近乎是一种缺氧的反应。她从来没想过罗海洛会这样地逼近自己,潜意识中认为这个笑容温雅的男子永远都是那样卓尔不群,虽然救过自己,但和她这等凡人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
可是现在,他真真切切地贴近她,他呼出的气息扑面而来,滚烫,灼人。
“我……我……”春袄低着头,语无伦次地“我”着。
罗海洛看着她小鹿般的模样,心情颇好地勾起唇,隐隐带着点不同寻常的邪魅:“衣服。”他轻叹,嗅着她身上还残留的酸臭味,提醒道,“去洗洗,臭死了。”他嫌弃地用手在鼻尖扇了扇,夺过衣物,转身大步离开。
“很臭?”春袄连忙闻了闻自己,一股另人作呕的酸臭钻入鼻间,她突然佩服起罗海洛的处变不惊来,这么臭都能那么淡定地靠近自己……果然乃神人也!
洗完澡睡回罗海洛安排给自己的客房,春袄给程母打了个电话。
“是春袄吗?怎么这么久都不给妈妈打电话?”程母温柔的声音在话筒中响起,春袄不禁捂住嘴巴,热泪滚滚而出。
“好,很好。”
“有没有饿到?衣服还够吗?需不需要……”
“妈,我很好。”春袄哽咽着声音,不住地点头。
“那……有没有见到……小深?”程母小心翼翼地问道,心中满是愧疚。
春袄心连着手一紧,白天程末深的冷漠和决绝的话语仍在耳边回响,深吸了一口气,她尽力地笑着:“没有看到呢。”
“我听说小深参加了你们大学的迎新会,怎么会没有看到?是不是小深欺负你了?给妈说,妈给你做主。”
那边的声音急了,春袄连忙摇头:“不是,妈。小深一直对我很好,你也不是不知道,从小就护着我,怎么可能欺负我了?”
“那可不一定,我们不是也没料到他敢在婚礼当天那样对你!”那天程母从来没有这么对自己儿子失望过,对春袄真心心疼。
“妈……”
“哎哟!都是我这臭嘴,咱别说这些伤心事,啊,咱就聊聊咱母女俩的事啊!”
她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全是程母问,春袄答,她笑着,眼里全是泪花。程家一直对她很好,收留她,抚养她,给她的爱一点也不吝啬。所以她也不能怪程末深无情吧?
程末深……我好想再叫你一声“小深”,然后你给我一个当年的微笑好不好?
这情好似毒药,扩散到春袄四肢百骸,当发现的时候,再高明的医生也无法拯救她溃烂的身体,发痴的心。
春袄蜷缩在床上,握着手机,话筒那头传来程母的絮絮叨叨,泪干在眼角。
也许……她程春袄没了程末深……就不再是程春袄了。
她不甘,却无力反抗。
她不想离开,即使用耍赖的方式,即使他厌她,恨她。
她不想放弃,即使在婚礼当天,她穿着冰冷的嫁纱,呆愣地听着他逃走的消息。
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就送梧桐子“ ”支持吧!
”支持吧!
已获得0个“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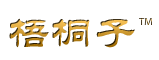
 河南省孟州市
河南省孟州市 山东省新泰市
山东省新泰市 广州市海珠区
广州市海珠区 安阳市 北关区
安阳市 北关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