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搬家
家乡区县: 德阳市旌阳区
“我等你。”糥糥的声音带着急切。
罗海洛看着文件,却又些恍惚。在某个话筒里,他也听到过那句糥糥的“我等你。”可惜,她却在等到他之前失踪了。
拿笔的手微微握紧,耳边响起那个人浑厚的声音“你名不正言不顺,想继承罗氏集团简直是痴心妄想!”那是来自遥远的声音,生生让他的命运偏离了轨道。
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握住,难受到无法呼吸。他微摇了摇头,将注意力集中在文件上。这样关键的时刻,他更要提起十二分的精神。
罗海洛说是几分文件,春袄却生生等到日落西山。期间罗海洛接到电话说是有人看见斯幕跟着程末深回了公寓,春袄才总算放心下来,倚在沙发上睡着了。
等到她被琴姐叫醒,办公桌上哪还有罗海洛的身影?春袄问琴姐,琴姐只说罗总有个饭局先离开了,吩咐她带春袄去对面那家甜品店,随便吃全记在他名上。
春袄有些生气,豪气地点了一桌子的甜品,闷闷地吃了起来。
琴姐做在对面直笑,问她:“春袄,你别跟罗总置气,他最近确实是忙。”
“哼!忙死他他也不能说话不算话吧?”春袄舀了一大勺布丁,入口即化,芒果的芳香溢满了唇齿。不愧是资本家才吃得起得东西,贵也有贵的理由啊!春袄默默地想,化悲愤为食欲。
琴姐见她这样,无奈地摇头:“那是笔重要的生意,听说还是关于你的呢。”
“我?”春袄停了下来,惊异道。她一个准备出道的新得不能再新的人,居然还有大生意?
琴姐捂唇一笑,两只眼睛都闪着无比崇拜的粉红泡泡:“你不知道罗总的实力,有罗总的帮助,你一定会一炮而红的!”
好吧……不是她的原因,而是她傍了个土豪是吧?春袄翻了翻白眼,继续吃。
“唉……你明天就搬到公司安排的公寓里去吧,听说你居然住在墨尚那儿?你和他什么关系?”
第一次发现琴姐也八卦,春袄道:“我能带斯幕搬过去么?”
“你还真住在墨尚那?”琴姐压低了声音,惊讶道。
春袄疑惑地眨了眨眼睛:“这又怎么了?”
“你……你你这样不是要气死罗总么?”
“嘎?!”
听了琴姐长篇大论外加一串申讨过后,春袄提着一大包外带甜品偷偷回了程末深的公寓。为什么是“偷偷”回?当然是琴姐一直认为罗大BOSS对春袄有意,为了不然春袄这支红杏出墙,琴姐十分周道地为春袄安排了一家五星级宾馆,免得春袄的贞操被墨尚给毁掉。
琴姐是不是想得也太多了?春袄有气无力地打开程末深的公寓,迎面就对上程末深若有所思的黑眸。春袄讪讪地将甜品带放在桌子上,正要转身就被一只手扯进一个炙热的怀抱。耳垂被轻轻地啃咬,春袄不由惊呼出声。
“别动。”低沉的声音,如红酒般醇厚醉人。他炙热的气息将春袄整个人都淹没,手臂霸道地圈着她的细腰,湿热的舌尖逗弄着她敏感的耳垂。
“别……”转过她的下巴,低头吻住那张诱人的樱唇,她的声音被吞噬在缠绵之间。
程末深的热情来得突然而狂乱,春袄一时承受不住,整个人瘫了下去。手掌托起她的翘臀,将她的身体整个圈在怀抱里,强迫她抬起头生生承受自己。
他肆意地挑逗着她胆怯的小舌,攻城略池。
“唔……”她要窒息而死了。
不舍地放开她的唇,舌尖还缠绵在她唇瓣,充满情欲的喑哑男音模模糊糊从喉间斯磨而出:“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
春袄心一颤,突然不敢告诉他自己马上要搬出去的事。
“那个……”斟酌了一下,春袄准备硬着头皮坦白。
谁知程末深搂着她就不放手了,把她放在自己大腿上,整个人闲适地靠在靠枕上,舒服地眯着眼道:“你说斯幕?正在屋里睡着呢。”
“我……我不是说这个……”春袄垂头搅衣角。
“你要搬出去?”剑眉一挑,程末深脸色微沉。
“是。”
“不行。”
“为什么?”虽然有些胆怯,但被如此粗暴的拒绝春袄一时还是有些受不了,她睁大了杏眼,不甘道。
眸子深深勾勒着春袄的五官,食指勾起她的鬓发:“你知道为什么。”
“……”
“不能搬出去,更不能……出道。”手下一紧,扯得春袄头皮有些疼。
她不满地夺回自己的头发:“喂!我凭什么听你的?”
“你本来就不喜欢不是么?”那双黑眸淡淡地盯着她,反问。
被轻易看透的感觉更不好,更何况这个男人半分没有给她留面子,从小就这样,任意地决定着她的所有事情。以前她不问世事,整个心都装着他,可她总是要长大的,总是要自己选择自己的路。
他不能再什么事都高高在上地帮她决定,不问她的感受。
有了十足的心理建设,春袄也就充满了底气:“你又凭什么知道我不喜欢?”
程末深一愣,看着那张上扬的小脸,皱眉道:“你从小什么个性我又不是不知道。”
“人总是要变得!”
“你不会变。”多么驽定的语气与不屑的目光。
春袄气鼓鼓地跳下沙发,完全脱离他的势力范围:“谁说我不会变!程末深,你听好了!我明天早上就搬走!”
“你敢!”
春袄只觉一阵天旋地转,整个人被按回了沙发上。春袄正欲挣扎而起两片男人滚烫的唇强压下来,他的唇舌不容拒绝地长驱直入,燥热的身体紧贴而上。
火热的唇在她身上肆意地点火,手指蔓延至她的敏感部位,因她下意识的低吟而更加卖力。
贴身的衬衫还整齐地穿在他身上,她的连衣裙却被褪到了腰肢,露出雪白的肌肤,和圆润饱满的酥胸。
意识到自己的模样,春袄脸不经红到了脖子上。她怎么这么轻易地就让……就让他……
可是当他紧密地靠近,他的气息充满她的全身时,她的大脑就完全当即,有什么东西就要破土而出。她不知道那是什么,隐隐有些害怕,又有些渴望。
“喂……干……干什么只脱我衣服?”杀了她吧……这样的话她都说出了口,春袄不经捂脸。
抓住她的小手,程末深低头啃咬着她的耳垂,在她耳边低笑:“别捂脸,帮我。”
“帮你干什么?”
“帮我脱衣服。”
“唉?你不自己脱?”
“我没空。”
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就送梧桐子“ ”支持吧!
”支持吧!
已获得0个“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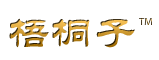
 河南省孟州市
河南省孟州市 山东省新泰市
山东省新泰市 广州市海珠区
广州市海珠区 安阳市 北关区
安阳市 北关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