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笑起来很好看(1)
家乡区县: 湖南省沅江市
在我的印象中,奶奶好像从来没有年轻过。打我记事起,奶奶的头上就顶着一头花白的头发,中间掺杂着几撮黑色发丝。
记得小的时候,我都是凌晨四点才起床做昨天留下的作业,昨天晚上我都顾着玩,看电视了。一到四点多,奶奶都会陪同我起床,我把作业本摆在餐桌上开始有模有样地写作业,而奶奶则在灶台旁为我摆弄早餐。
直到小学四年级,我去了深圳读书,她跟爷爷两人守着一栋三层的楼房。再往后,爷爷去世,楼上只剩奶奶一人居住。每次过年回家,当车子停在楼房下的停车位时,我都会第一时间开车门跑到大门前,朝三楼大声喊,奶奶,我是二弟。不久后,便能看到三楼窗户伸出一个可爱,圆溜溜的脑袋,奶奶会一边格格地笑一边朝楼下喊,你们回来啦,我去给你们开门。那时候只知道,奶奶爽朗的笑声能解决世间所有的难题,不曾去想过,在这之前,奶奶独守空房苦等了多少个日夜。
奶奶在那栋空楼里独自居住了两年。以前都是我跟她睡在一张床,我睡里面,她睡外面。有一次,我睡得太死,睡觉的习惯又不好,竟一脚把奶奶踢下床。那时,奶奶筋骨还算硬朗,当时,我楞没发现,是多年后,她才当笑话讲给我听的。
初中的时候,她来深圳,晚上原本想让出一张床给奶奶一人睡,但奶奶说,想让我跟她睡。那时不懂事,只知道奶奶有糖尿病,想着若是跟她睡在一起,没准会沾染上什么病。奶奶执意要我跟她睡,我推说,奶奶,你忘了,小的时候我还把你踢下床呢,我怕又一次踢你下床。奶奶拗我不过,只好作罢。直到后来想到这事,猛的一醒悟,觉得自己怎么能这么混蛋,在心里暗自咒骂自己不是人。不知道那天晚上奶奶是否暗自落过泪。
前几天,我表哥从老家把她载到深圳,我让她先在这边住一晚,隔天再去大姑家。奶奶一开始还特别不安,问了我好几次:那你跟你弟睡哪啊。我不厌其烦的跟她解释:没事,我弟睡上铺,我跟你睡下铺。那是我们相隔十几年后又一次睡在同一张床上。仿佛回到了小时候,夏天很热,奶奶握着把蒲扇,在我头上,为我扇风,哄我入睡。
那天晚上,我们躺在床上,迟迟未睡,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但大多数时候都是我听,她说。奶奶谈性还是那么好,记性却已不如从前,有些事会重复好几遍,而于她,仿佛所有的一切都是第一次述说。她时不时会从一件事情中转过话头,突然问我,钱够不够花啊,不够奶奶这里有。我回她说,够的。她会经常性地跟我确认这个问题,有时会觉得她唠叨,但却不感到烦,反而很享受回答她的过程。
睡到半夜,奶奶说要起床尿尿。她股骨头处做过两次手术,起身有些困难,我起来扶她起身,奶奶小心翼翼扶着铁架子一步一步挪到厕所,我在一侧搀扶着她。上完厕所,奶奶还是一步一步地挪动着到床边,她不太敢一下子躺下去。我用手扶着她的后背,她缓缓地,像升降机往下降一样,头一点点地往枕头靠,等终于跟枕头接上轨后,奶奶脸上露出一副苦尽甘来的神情,我心里不自觉纠了一下。
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就送梧桐子“ ”支持吧!
”支持吧!
已获得0个“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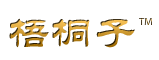
 河南省孟州市
河南省孟州市 山东省新泰市
山东省新泰市 广州市海珠区
广州市海珠区 安阳市 北关区
安阳市 北关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