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天清雨
家乡区县: 云南省水富县
文案:
“风吹晚林,去不留声,任它疾驰过,而我自清雅。晚清亦挽清。倒是个好名字,但我比宋砚之还要年长一岁,可以叫你‘挽挽’么”。
他叫我名字的时候,声音沉郁低缓。仿若前年我在寒山寺山脚的青石板上小憩歇脚时,听到的远山古刹的晨钟暮鼓。清润而又不失韵味,好似要直直敲到心底去,令人颤然通透。
2011年入冬以前,因为家庭变故我只身北迁到济南。寄居在母亲故友住处,她将我托付在此。也是家里出事之后我才知道母亲那样矜贵自持的人儿居然会有这么不着边际的小友(虽说是故友,但是母亲年长她近十岁)。
在成都的时候,族里的婶娘们背地里都说孟荣华的那个小女儿性子如何如何不讨喜。可是与宋璟相处的那几年,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地不讨喜,那简直是讨人嫌里边的个中极品。
所以说,没见过世面的女人大多是可怖的。她们会扎堆跟石榴般攒在一起,经常闲得蛋疼地轻易给你下个定义,可能这个标签一旦成形,就要背负一生,这对一个女人来说着实是极重的。
这大概是最初鞭策我玩命儿读书去见世面的根由吧,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不止一次这样想过。
很早就知道小香要将我送走,可真到了事情发生的时候,却心慌地觉得自己好像还未做好准备,左手手指兀自地变幻很多种高难度动作,拧巴在一起,看上去倒是很符合当前的心境,其实再过半年我怕是依旧也做不好准备的吧。
母亲开车将我送到双流机场。登机前,她站在通道口搂着我,虚握着我的手,柔声安抚:“挽挽,宋璟她是十分好相与的人,定会待你极好的。不要再同以前那样愁眉苦脸,要常笑笑。就像这样,我们家挽挽是个漂亮的小姑娘。”她左右手提着我的嘴角,扯出一个笑。我想着当时其实应该是丑爆了吧。
我抬头看见流线型穹顶完美地垂落下来,透过被割裂成数块的玻璃,上面映照的是刚从跑道上起飞而过的巨大机翼。高分贝的轰鸣声仿佛是为我的形单影只而做的哀吊。
“等到来年 仙客来 开花的时候,我就去接你好吗。”
我狠狠地点了点头,更加抱紧了母亲,软软地哀求道:“妈妈,你可以把今年腊梅的花瓣拾一拾,给我做个干花枕头嘛?枕头会不会太大了,那给我缝制个香包也是好的。我早就想要了。”
她理了理我的头发,笑得美艳动人。“好的,都给你做一份。到了那边要记得给我写信。”
我闷闷地应了声。
孟荣华是我母亲,大家惯叫她小香,我在私底下也跟着这么没大没小地叫,却从不曾遭过训斥,这大概与母亲格外宠溺我脱不了干系。
而父亲在我四岁时就离了家,整整八年杳无音信,家里人也未在我面前提起过他去了哪里,干了什么,仿佛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一样。只是隐隐地听家里的小辈们乱嚼舌根他在外面有个情妇,然后一起跑了,还有的说因为欠了外债,打死了人,进了监狱,总之版本很多让人眼花缭乱。我那时候刚刚是虚荣心开始作祟的年纪,况且无论哪个版本都对我和小香产生了极大的伤害。这样父亲着实让我看不起,也就随大流忘记了这号人物。
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就送梧桐子“ ”支持吧!
”支持吧!
已获得0个“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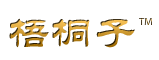
 河南省孟州市
河南省孟州市 山东省新泰市
山东省新泰市 广州市海珠区
广州市海珠区 安阳市 北关区
安阳市 北关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