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明题&小妖UU(中)
家乡区县: 重庆渝中区
4.
夜幕降临,几个少年嬉闹着拍着篮球走出校门,宋琦依旧没有给我打电话,难道他已经铁了心不再爱我了?
我叹口气,将戴宇的地址抄下来,又看了看照片上那个忧郁的少年,这才合上他的档案。几个班干部对戴宇的评价都很低,甚至嗤之以鼻。他从来不主动和班上的同学说话,更不会参与任何集体活动。他独来独往、表情冷峻,行为怪异。有个胖胖的女生从小学时便和他是同学,她一提到他就会浑身颤抖。
她说,戴宇家养的小动物从来都不会活过一个月,他买它们来,就是为了慢慢地将它们折磨死;她说,戴宇的爸爸不知为何在他六年级的时候上吊自杀了;她说,戴宇的妈妈也在去年冬天跳湖自杀了,春天在湖里打捞出的第一具尸体就是他的妈妈。说到这时,几个同学七嘴八舌的跑了题,他们都觉得最近接二连三的自杀事件是因为他妈妈冤魂不散。
说到最后,那个胖女生仿若突然想起了什么,拍着大腿说道:“老师,有件事不知道该不该说……初中的时候,戴宇曾经暗恋过一个女生,在他暗恋她的绯闻传开之后,那个女孩就被淹死在湖里了,那时候大家都传言戴宇是凶手,只是谁也没有证据……”
听到这里,我莫名想起戴宇在讲台上的话,于是心一点一点地沉下去,一直沉进无尽的黑暗里,那黑暗中充斥着污浊的酒气,妈妈的脚悬头顶,随风摇晃着。
戴宇的家在人造湖附近的老街区,破败的街道两侧,是破败的老式职工宿舍楼。楼梯的感应灯坏了,忽明忽暗,楼梯两侧的墙壁上画满了凌乱的涂鸦,仿若十八层地狱一般狰狞嘈杂,那些涂鸦密密麻麻一直延续到3楼,戴宇就住在这一层。
那个曾在湖边见过的小女孩低着头坐在楼梯上,怀里抱着一只脏兮兮的京巴狗。听到脚步声,她依旧垂着头,将瘦小的身子向墙的里侧靠了靠,大抵以为我只是路人。
我蹲下来,轻柔地问:“你叫什么名字?你哥哥在家吗?”
她一愣,将怀里的狗搂得更紧了,生怕别人抢走似的,她的声音依旧怯怯的:“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要是我告诉你我叫戴安,告诉你哥哥不在家,你就会把我拐走是吧?”
我微笑着,表扬道:“真是机灵的丫头,你这么做是对的。不过我可不是坏人,是你哥哥的老师。”
这时她才站起来,仰起头,我不由惊呼一声,捧住她的脸:“额头怎么伤得这么重?”她的额头有一块杯口大的新伤,血似乎刚刚止住,看起来湿漉漉的。
“关你什么事?!”戴宇突然出现,他一把推开我,将妹妹掩在身后:“你来这里干什么?!”
“家访。”我说。
戴宇阴冷地扬扬嘴角:“那你来错地方了,你若对我家访,恐怕得到阴曹地府了。”
“戴宇,”我尽量让自己表现得和蔼可亲:“我只是关心你。”
不知为何这句话反而惹恼了他,他猛地将妹妹推进门内,恶狠狠地说:“我可以容忍别人忽视我、鄙视我、嘲弄我、甚至虐待我,却唯独无法忍受别人关心我!”
说罢,他“嘭”地一声将我关在门外,楼道的感应灯们霹雳巴拉亮起来,又霹雳巴拉的闪烁着,刚才躺在戴宇妹妹怀里的小狗蜷缩在地上,半个脑袋已经被砸得血肉模糊——原来它早已死了。
门内,隐约传来戴安的哭泣:“哥,狗狗不理我了……哥,为什么狗狗不理我了……”
5.
宋琦不理我了,为什么宋琦不理我了?这句话一直回荡在我的梦里,后来变成了戴安的尖叫,她颤抖着从指缝里望着戴宇,一直喃喃地哀求着:“不要杀死它……不要杀死它……”小狗的哀鸣直冲屋顶,接着,那哀鸣又变成了父亲的。父亲又像小时候那样喝醉了,他把母亲从屋梁上摘下来,然后骑在她身上左右开弓,母亲的头像拨浪鼓一样摇来摇去,摇得我头晕目眩。我必须制止父亲,否则我一定会被母亲的头搞晕的,我从厨房拿出菜刀,深深吸一口气,卯足了全身的力气……这时,戴宇出现了,他冷着脸问:“你能证明我是杀人犯吗?”
闹钟将我从嘈杂的梦境中挽救出来,我疲惫地擦擦额头的汗珠,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戴宇和我一样,都是好不容易才长大的孩子。他向我提出一道证明题,需要我用心去解答。
事实证明,无论我曾经历过怎样的磨难,我依旧太天真了,我低估了戴宇。
当我将他带到教务室,推心置腹地和他谈心,甚至不惜告诉她我小时候的经历以期获得他的信任和共鸣后。
我告诉他,我从小生活在不幸福的家庭,父亲因为我是女孩,根本不爱我;我告诉他,父亲经常酗酒,最后逼得母亲上吊自杀;我告诉他,在父亲殴打母亲尸体的那晚,我用菜刀将父亲砍成重伤;我告诉他,父亲为了得到另外一个女人的爱,曾假惺惺地爱我过几天,为的是哄我吃下有毒的甜点;我告诉他,父亲杀我未遂被判刑,病死在狱中;我告诉他,我如何在养父母的冷眼中长大;我告诉他,我如何和养父母的儿子宋琦相爱;我告诉他,宋琦又如何离开了我。
我把伤害累累的心袒露在他面前,是希望他明白,无论怎样的苦难,也不应让我们失去对生活的热情。不想,他听完了这一切,只是淡淡地笑了笑,然后从怀里拿出一枚脏旧的MP3,轻轻按了某个按钮——我的悲凉的声音从那里缓缓流出。
他收起它,站起来,惬意地伸了个懒腰,然后说:“老师,你的人生真悲惨,真动人,真令人怜惜,我想,明天全校所有人都会通过校园网的音频,知道你的故事。”
“你!你变态!”我愤怒地站起来。
他依旧笑着:“我变态?那么,经历了这一切的你,现在你,正常吗?你觉得,学校会让一个有着心理阴影的人当老师吗?你觉得,同学们会喜欢有着这样不堪过去的老师吗?”
“你……”
“嘘——”他凑过来:“老师,我其实不是坏孩子,我可以不把这段音频放到网上,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不要再干涉我、和我的家事!”他重点强调了“家事”,这两个字提醒了我,我想起了戴安,那个伤痕累累的孩子。
“你在虐待你妹妹!”我厉声道。
他一愣,随即摇了摇手里的MP3:“老师,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不要干涉我的家事!”
6.
在“受虐的戴安”和“我的前途”之间,我进退两难。我想过报警,但在之前,我必须证明我所知道的一切都是真实的。自从童年时父亲对我虚情假意的爱过几天后,我便对这世间的一切充满了怀疑,我变成了一个热衷于证明的人。
我决定挽救戴安,那个女孩深深牵动了我的心,我的脑海里时常会冒出戴宇虐待她的画面,时常会冒出那只被戴宇虐杀的小狗,我必须帮助戴安,不仅仅是害怕重蹈那只小狗的覆辙,更重要的原因是,她像足了小时候的我。
那几天,戴宇时常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在我的目光落到他身上时,冷冷地扬起手,晃着那可恶的MP3。更可怕的是,不知从何时开始,他开始跟踪我了。
他总是在放学后站在校门口的门柱后面,耐心地等着我,然后不远不近、不紧不慢地跟着我,就像一头信心十足的狮子在漫不经心地玩弄着手中的猎物。
那几天,我特别想念宋琦,有好几次都准备拿起手机主动拨他的电话,可每每拨出两个号码,就懊恼地重新将手机收起来。他若爱我,早就该主动联系我的;他这样一直不肯露面,定然是不爱我了,既然不爱我了,我又何必自讨没趣呢?
终于,我忍无可忍,再次来到戴宇家,来之前,我告诉那个胖女生:我要去做戴宇的家访,如果一个小时后我没有给她打电话,她就报警。
楼梯里的感应灯依旧没有修好,大抵永远也不会有人来修吧。
戴安照旧坐在门口的台阶上,低着头抱着那只已经发臭的小狗,嘴里哼着某支熟悉的童谣。她抬眼看了看我的皮鞋,目光顺着我的裤腿慢慢爬上来。
她抬起脸,额头的伤口尚未痊愈,脸上又多了一道新鲜的刀疤,从嘴角一路蔓延到耳根。戴安轻轻放下小狗的尸体,漠然地看了我一眼,从地上拿起一截蜡笔,像曾经的戴宇一样,掰成一小截一小截的,然后用最后那截笔头,在墙上画着凌乱的画。画里的每一根线条都强悍而犀利,带着某种恶狠狠的不甘。
我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戴安,疼吗?”
她继续画着,背对着我,摇摇头。
“是因为哥哥吗?”
她点点头。
“阿姨带你走好不好?找个真正懂得爱你的人家……”
她突然转过身,捂住耳朵,蹲在地上尖叫起来:“从你对着哥哥笑的那一天,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你打算要这样做!”
楼下一阵仓促凌乱的脚步声,戴宇气喘吁吁地跑上来,他气急败坏地将手里的馒头甩在我身上,低吼着:“滚!”
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就送梧桐子“ ”支持吧!
”支持吧!
已获得0个“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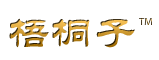
 河南省孟州市
河南省孟州市 山东省新泰市
山东省新泰市 广州市海珠区
广州市海珠区 安阳市 北关区
安阳市 北关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