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
家乡区县: 湖南省长沙县
那个男孩叫陈兵。
就算是在近十年后的今天,我坐在静悄悄的异地,敲出这两个字,也还是会忍不住停顿一下,郑重地吸口气。得贴近了电脑屏幕仔细地辨认。耳东陈,丘八兵。陈兵。
高一的下半学期,新转来一个学生,他站在讲台上,语速缓缓地做着自我介绍。“耳东陈,丘八兵。我叫陈兵,大家好”,说完一笑,露出几颗耀眼的牙齿。我当时个子矮,坐在第一排,视线刚刚高过讲台,瞅见那家伙,他竟然好看得呀,像流川枫一样。
丘八陈的话音刚落,紧跟着就是一阵暗暗涌动的骚动,女生的、男生的,骚动里各怀鬼胎。而我,脸一红,有一点点心动。班主任清了清嗓子,说:陈兵,你坐四组最后那张桌子。
陈兵“嗯”一声,径直朝后走去。班里人太多,最后的桌子贴着墙。我看见他拉凳子、把书放进抽屉、像跌倒一样坐下,duang一下。
四组靠着墙,最后的位置有扇大大的玻璃窗户,窗外是走了样子的山,山上有几棵树,枯枯的。春天了,可草还没长出来。教室里一派喧哗,男男女女,出来进去,闹腾的,似乎有折腾不完的活力。我慢慢转过身,一面心不在焉地看后排的男生做作业,一面偷偷地瞄着四组最后的陈兵。陈兵正望着窗外出神。那一刻,我猜不见他看到了什么,而我,一双眼里,全是他的侧脸。
过了许多天,我几次假装去后排借尺子,几次假装去四组找课本,几次故意大声地收作业,好几次咋咋呼呼,可是,都没能跟他说上一句话。陈兵的一张脸,始终淡淡的,像白开水装在玻璃杯里一样,平平展展,看不见起伏,甚至,看不见水。那么多的许多天之后,我唯一斩获的消息是有次去班主任家里吃饭,她无意间说起新来的学生,说他已经高考过一次,考得太烂,才换到我们学校从高一开始重新念。班主任叹了口气:挺聪明的孩子,怎么那么热衷于谈恋爱。
我低下头默默吃饭,班主任的最后一句话,一石激起千层浪,在我小小的心里,翻来覆去地滚动着。哦,原来他恋爱着,怪不得总望窗外。
那扇窗外,或许就藏着他的姑娘吧。
自那之后,有一段时间,我强迫自己:别去关注他,别去关注他。也倔强地不肯转过身子,上课了看黑板,下课了也不太动,悄悄拿本小说,把头埋在桌子下面看。可看到有爱情的地方,总能千回百转地回到陈兵身上。
蠢蠢欲动,春天在动。那段时间,我把一个蠢字演艺的活灵活现,在心里牛逼哄哄地想:有什么呀,有什么呀!
直到很久后的一个晚自习。我第一个冲出教室,没什么特别的理由,就是觉得上够了自习坐够了板凳急需奔跑急需吹一下冷风的那种。可是那天,我还没来得及迈出教室,就被一个人从后面给撞了一下。那个人擦着我的肩膀挤出了教室,直到他走远,我才慢慢反应过来:是他。陈兵。
我摸着自己的那一侧手臂,觉得温柔极了。我没有像以往那样冲回宿舍,而是失魂落魄地去了操场。操场静静的,静静的躲在情侣的脚下。我慢慢地朝黑暗走去,离路灯越来越远,离黑夜越来越近。说不上害怕,只是愈走愈坦荡、平静,为着那一点点不留余地的温柔。像把所有的所有的东西都想通了一样。
就是在我把所有东西都想通了的时候,意外地听到暗处传来声音,说:我来一中,第一眼就喜欢上你。那个声音很熟悉,像谁的呢。另外一个女声答:你不是有女朋友吗?那个声音呵呵笑了:从前的事了。
我听着他们对话,走出去好远,才想起来,那个熟悉的男声,是陈兵。好奇心大过了一切,我就那样定定地立在黑夜里,盯着声音的地方,直到看见模模糊糊两个人影。人影牵着人影的手,向路灯一点点靠近。那个被陈兵牵着的女孩,竟是我们的班花。
平时并不见他们说话。怎么就……在一起了?
我东游西荡了很久,才慢腾腾地回宿舍,摸着黑爬上床,隔着窗帘看暖黄暖黄的路灯,没来由地觉得自己的青春期可能就这么过完了。
第二天,昏昏沉沉地去上课,坐在第一排,不说话,不回答问题,全力以赴地跟全世界生气。拉长一张原本就不美丽生动的脸,说不出个所以然。后排的男生拿铅笔戳我,我懒得回头。他再戳,我就转过身,恨恨地看他一眼。我从那个男生的眼睛里,读到了自己的愤怒,而那个男生,脸微红,一句话也没说出口。
可是,那天,陈兵像计划好了一样,并没有来。没有来的,还有班花。
我又开始了贱贱的焦急。怎么了?没有人知道。
直到下午,他和她才出现。像约好了一样地一前一后进了教室。我似乎看见,他们的爱情故事正在暗度陈仓。而作为一个根本连故事边都没挨上的多情少女,我竟然生出来一股“望尽千帆,恨比水长”的怨气。
我心深深处,中有千千结。这样晦涩难言的青春期,我一直行云流水地过到了高三的下半学期。期间,陈兵从班花,换到二班的班花,再换到邻校的美女,接着是某医院的小护士,班上的一些男生会在课间休息的空档跟陈兵开玩笑,班上的女生也嘻嘻哈哈地给他介绍对象。而几年来,我竟还是没能和他说过一句完整的话。默默的,默默的,像黑白电影一样,演给自己看,也只能自己看。我也终于懂得了班主任老师的那一声无奈的叹息:挺聪明的孩子,怎么那么热衷于谈恋爱。
怎么就那么热衷于谈恋爱?
怎么就不能是我?
有些问题,一辈子都不会有答案。
比如,可能陈兵连我的姓名都没听说,听说了也肯定不会写,就算会写也一定写错。
良辰美景奈何天,为谁辛苦为谁甜。
高考前的那一段时间,老师打乱了座位,我很幸运又很不幸地跟陈兵入了一个小组。我是小组长,带领大家写作业、做测试,陈兵总迟到,我不好意思指责他,憋了很久才小心翼翼地说:那个,你以后来早一点吧。这是我和他说的第一句话,我记得当时他愣了一下,“嗯”一声之后就趴下不动。
不过,从那以后,他确实肯来得早,大多数时间里,竟然是最早的那一个。有一段时间,我进了教室,总能看见他穿着白色短袖,坐在空荡荡的教室里,也不知在想什么,呆呆的,像幅漫画,说不出的感人。这时候我往往不敢待在教室,拿本英语书,匆匆忙忙躲在走廊里,选一个能恰好看见他而不被他看见的地方,乖乖地立着,看一眼单词,看一眼他。那时候我总想,假若能一直一直这样,我看他,他看风景。
一切的假如,都是一厢情愿。直到高考前放假,他都没能好好看过我一眼。他和所有人说笑,却避免同我讲话。而我,始终严肃,像班主任一样,一个严肃的少女主任。
就这样,时间在他的沉默飘忽中,以及我的神往忧伤中,像黄河在黄土高原的水一样,哗啦啦地奔腾,一去不复返。
转眼,高考仅剩一个月。在大家如火如荼地备战高考的时候,他却突然变得话多。会主动跟我说话,说许多话。讲他自己,说他以前学习可好,后来就越来越不好,参加过一回高考,没考好,就来这里从高一开始重新学。这段经历,常让他悲伤。我没有告诉他,这些我都知道,知道了三年。
他还说他谈过可多场恋爱,有师范院校的大学生,有校花,还有不上学的护士。他说每一次恋爱他都很认真,就是到后来发现女人跟女人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就失掉兴趣了。我也没有告诉他,这些我都知道,一直都知道。
他说:你是个好姑娘,我希望能跟你做朋友。“好朋友”,他特意加了一句。
我不说话,静静地听着,也不看他,就做自己的事情。心里却,翻江倒海。想哭哭不出来,那样的酸涩,连自己都不能懂得。
高考的最后一节考完,我走出教室,下了楼。
有光跃入视线,陈兵站在楼下,正看我。看见我,眼睛亮了,把右手扬得高高。一阵风吹来,人渐渐多了,我藏起自己,绕过他,出了门。沿着夏日的小路走,越走越想哭。到后来就真的哭了起来。难过得,就好像明明有一张人民币躺在脚下,可自己就是弯不下那个腰。为什么弯不下腰?
那个大学,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能考好。最后就去了一所不情不愿的大学,学一些不情不愿的专业。于是,爱情就成了那些个失意人的主业。
我当时看了一眼我们班四十几个人,三十几个女的,为数不多的几个男生,也很快被瓜分。我不知如何表达我的失落,朋友都离得那么远,能讲话的人也没几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我内忧外患,只能拐弯抹角地想起了陈兵。
可是,陈兵去了哪里?
为了找到他,我试着跟很多人联系,还好有个校内网,让我们不至于失散。找了很久,他竟音讯全无。直到某天,一个陌生QQ拉我入同学群,群主恰恰是他。我看着他的名字,有一种“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失而复得之感。
我打开他的个人资料,加他为好友,附言,我是某某某。很长时间都没反应,直到第三天的下午,我的QQ才响起来。他加了我。
也没有聊。我就那样默默地看着,就像多年前一样,只看看。看到就好。
那时候,宿舍里的都在谈恋爱,每天晚上,大家躺在床上交流恋爱心得。她们都鼓励我:既然喜欢,就去试一下啊。刚开始,我也没往心里去,呵呵笑着,继续听别人花前月下。在别人的花前月下,展望一下那份属于我的没有发生过的爱情故事。
有时候,叫人行动的不是爱情本身,而是因爱情而起的虚荣。她们说得多了,我忍不住慢慢地心动了,也偷偷地模仿着她们示爱的方式,折幸运星、折千纸鹤、打电话、送礼物。而我,我那么笨,最后也只能选择自己的方式。写信。
每天晚上,我背着书包去自习室,一个人冷冷清清地坐着,慢慢地写,一笔一划,写满了一张纸,又一张纸。如此坚持,写了一年。等我做足所有准备、充足了所有勇气准备去找他的时候,已经有了三百五六十封信。
那天晚上八点,我终于点开了他的QQ号,敲出了憋了一年之久的两个字:在吗?那之后,我就对着电脑屏幕,什么也不做地等。等到宿舍熄灯、电脑黑屏,也没收到回复。
收到他的信息,已是一个礼拜以后。他说:你好,你是?
那一刻,我的心里像被砸开了一个大洞,那洞里有风,呼呼地吹,吹得二十岁的我,站也站不住。
我让自己冷静,再冷静,敲出了一行字:我是小组长啊,你还好吗?我来看你好吗?删掉,重敲:我是木木,你的高中同学。删掉,重敲:你猜。删掉,重写:我是……
我是他的谁。
敲到最后,删到最后,我竟然对着电脑屏幕一阵没声音的乱哭,眼泪掉满了键盘。宿舍的人问:你怎么了?对啊,我怎么了,我怎么解释了。我摇摇头,抹掉泪,不说话,又把他删掉了。
之后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再写信,也没有去翻那些写好的信。所有故事似乎都回到了最初。五月八号是他的生日。我通过很多同学打听到他的校址、专业、班级,找了个盒子装好那些信,贴张邮票,寄了过去。
至于,他收到没有,我不得而知,也不想去弄清楚。收不收到又有什么关系,我只是把从前的自己打发掉而已。
时隔多年,坐在电影院里看《匆匆那年》,方茴在雪地里奔跑、哭泣,一地的雪,漫天的风,她孤孤单单寻找陈寻的名字。
我一时没忍住,哭得哗啦哗啦的。
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 就像那年匆促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 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别太快冰释前嫌 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 我们要互相亏欠要不然凭何怀
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就送梧桐子“ ”支持吧!
”支持吧!
已获得0个“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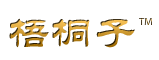
 河南省孟州市
河南省孟州市 山东省新泰市
山东省新泰市 广州市海珠区
广州市海珠区 安阳市 北关区
安阳市 北关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