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旧镰刀
家乡区县: 阳江市江城区
四月天,我想给阿公打扫一下房间。刚一进去,就发现老屋斑驳的墙上赫然挂着一把镰刀,如一弯腐蚀了的月牙,低诉流年飞转。阿公九十多岁了,他的脚刚刚告别了田野,但他的眼睛时不时地对视与田野相依相偎了一辈子的镰刀,恰似两个老朋友无言的对话。
镰刀已经锈迹斑斑,但木把明晃晃的,似乎散发着油汗香,幽幽柔柔地纪念着阿公对它的知遇之恩。阿公常常会抚摸木把,却从不触摸刀部。导致这把镰刀极不协调,上半部似老掉牙的百岁老人,下半部却像一位温润的少女,还带有体香。
陪伴阿公的许多人许多物,都渐行渐远了。先是一个个孩子,像蒲公英一样飞到大城市,漂泊了一阵就在那定居。后来阿公有了许许多多的孙子孙女,可阿公听不懂他乡的语言,孙子孙女们又不懂阿公的乡音,且子孙们少回家,倒是阿婆天天陪着阿公。阿婆阿公守守着一亩三分地,春天来了,慢慢播种。夏天来了,慢慢杀虫。秋天来了,慢慢收割。冬天来了,慢慢等春天。慢慢地,一起看季节切换。病来病往,几把老骨头还算硬朗,偶尔还能给子孙们留点农村米,自己一颗一颗种出来的,吃得舒坦。
那个冬天太长,阿婆等不及,匆匆走了。收稻谷的是镰刀,收阿婆的是命运。稻谷长于土,吐出谷粒后又归于土。阿婆劳作于土,反复收割稻子,无力了,长息于土。在田埂的不远处继续守着这片土地和阿公。不久,阿公年事已高,不能劳作,只能在田埂走走看看。
唯有这把生锈的镰刀,依然陪着阿公。曾几何时,阿公割稻回来,总要磨磨它,它也争气地似上战场的宝剑,闪着凛冽寒光,帮阿公拿下不少战利品。
不劳作的时候,阿公摸着它像抚摸自己的婴儿,无限温柔。镰刀挥舞的时候,毫不逊色于战场上的厮杀。最后总是稻子被征服,缴谷投降。现如今,阿公恐怕连弯腰都很难了,这片或绿油油,或黄灿灿,或褐着等待春天的土地,一成不变地荒芜,荒芜,不再生动,正如一个植物人没有任何的表情。多好的土地就这样废了。阿公的心扯得发疼。
屋子仍挂着这把镰刀。没事的时候就看一眼。这把镰刀曾割破他的手,割破他的脚,那不省油的稻叶也曾划破他的额头,稻叶上那细小的锯齿划破皮肤也是要见血的。可阿公从不把这点伤当一回事,吐口水擦擦,继续弯腰割稻。那深深浅浅的伤痕就印记入他的身体,记录阿公的命运,稻子的命运,镰刀的命运。那时候的天空,也曾有乌鸦忽地掠过天空,抛下几声凄厉的噶噶。偶尔有几只燕子飞过,倏地闪到电线杆上,只看到几条长长的线点上了几个小点点,像阿婆用黑豆发的豆芽。也曾有风吹过,混着淡淡稻谷香,稍微抑制一下汗水的泛滥。也曾有蛙叫在晚上,头顶还有一轮或圆或缺的月亮。
那时候,阿公总是笑呵呵,只要有镰刀,有地,有一把硬骨头,就知足地在土地匍匐前进。土地是硬汉子,不容易征服的。阿公推着犁铧,光着脚,把土地的心事一点点地揭开,用阳光炒一炒,蘸点雨露,泥土开始湿润,柔软,如恋爱着的女人,准备孕育全新的生命。这时候,泥土混杂着阳光的味道,雨露的味道,阿公汗水的味道,那是泥土特有的孕味。
累了,阿公甩下草帽,垫着屁股便坐下。喝一碗水,抽会儿烟,静静地看着自己种的稻谷一点点地发芽,吐出细小的嫩芽,稀稀疏疏的绿色点点,慢慢地丰满成绿油油的一大片,然后一点点地变黄。当稻穗谦卑地低下头,准备谷熟蒂落时,镰刀便准备出场了。手握镰刀,收获的喜悦甜上心头。阿公得跟镰刀好好磨合磨合,好让镰刀衍生成阿公的带刀的手,捧回一颗颗饱满的稻粒。力度、高度、角度把握不好,谷粒被吓到,落入泥土,阿公就得一颗颗地捡起来。每次割稻之前阿公在磨刀石上吐口水,然后慢慢地磨,唤醒镰刀的刚性,镰刀越是锋利,水稻的分娩过程就越短,阵痛越少。
这把旧镰刀,挂在墙上,如过时的日历。除了阿公,没人理解镰刀的情义。蛙叫虫明的夜,火烧云漫天的傍晚,日出冲破云层的早晨,阿公在等待,等待有人来听听镰刀的秘密,等待有人再次唤醒镰刀的刚性,为稻谷接生。
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就送梧桐子“ ”支持吧!
”支持吧!
已获得0个“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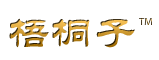
 河南省孟州市
河南省孟州市 山东省新泰市
山东省新泰市 广州市海珠区
广州市海珠区 安阳市 北关区
安阳市 北关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