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河风土志(二)
家乡区县: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
绥远社临河通讯 本县为绥西重镇,北依狼山与外蒙古毗连,南与乌审旗接壤,西以乌拉河隔宁夏,东以昭和渠界五原。黄河横贯其境,杨家河、黄突龙亥河、产金河(永济渠)等大干渠水势畅旺,灌溉极便,支流如网,地质肥沃,产以小麦、糜子为大宗,常称之为“绥远的米粮川”。
荒古的风味
临河的社会依然滞留在荒古,仅仅学上了初期的农作阶段,地虽经垦,大部仍为草原,红柳、竹机、哈木耳、苇子,丛丛密密,高四五尺许,沙凸间其中,常行走半日,不见一人。偶有之,非草棚似之蒙古包,即似茅庵之小屋,高约三尺,围以小墙,盖以木椽数条,前留小门小窗各一,屋前为堆置灰土之所,此即乡民之居宅也。野多蒙民牧女,身着长袍,腰捆红缎,长毛巾包头,傍系珠珠耳垂,足登长靴,道路不整,迷途无人指,询之无人对,着军服者,土人皆敬畏,食宿随处可,通蒙语者,蒙古包中宿食与自家无异。
交通与耕耘
一、临河设有三等邮局,每月来往信件十次,省垣寄之信件,半月始见回音,陕坝、蛮会有足差,两日往来一趟。杨家河亦有足差一人,往来时日无定。临陕安有长途电话,消息灵通,省垣拍致之电,三日可到。二、土人往来多乘马,载重以车,大小与常见者等,车轮特别大,高四五尺,辕口横一木条,搁牛膊上,行动笨滞。耕耘的方法很粗单,上粪那是从未有过的事,犁地也不常见,春间耙过就耘,勤劳时锄一遍,懒时连一锄也不,芦草高过麦,草苗齐生并长,有地皆然。水到地头,却是拼上命也要浇。
可恶的渠头
常言“包东资天,后套靠河”,除刮黄风外,全年也得不着三寸雨水,老百姓全靠着黄河过活,年年的修渠费、水租,不知要花多少。每渠有好几个渠头,这些人都是由大户指派的,遇到浇地,小佃户就得给这些渠头爷们送礼、请吃饭、许粮,顺不了这些爷们意,水到地头也是浇不上。
城市与政治
城市的房舍也与乡间无异,四合头的院子看不到,却是些“就院取土,垒墙四堵”的临街房,留个小门,挖一窗空,屋内黑暗,家家土炕上放盏烟灯,老常红日三竿烟筒里才见冒烟,人静总在十二点。临河素以肥富著称,历年执政人员,无论有能无能,胥以赚钱为事,建树毫无。设治数年,鲜有进步。盗匪不防,河年泛滥,淹没无常。街道失修,城垣倾破。陕蛮两处之街基地,迄未放卖,一任户家凭力争占,纠纷时有。财建两局长向由李杨两姓分任,收支无度,概无预算,积病种种,从未清理。差徭局需一索十,大斗凹模,民多隐恨。公安局长向多不称职,民十九郭凤山驻军哗变,枪械全失。街道污秽,尘土飞扬,市民随地便溺。警兵服装褴褛,形同乡下佬儿,守坐门前,几不识其为岗警也。城内路灯绝无,东关安置一二暗淡不明的路灯,深夜行人颇感“风吹行路难”之若!区长权限高于县长,向由李杨任傅四董事充任,公所设于各家府内,收回的粮倒于其仓,收回的钱,放于其库。公私相混,别无尺度。民十九后由民厅派员接充,重建公所,高悬虎牌,形同衙门。一二区长,被控交卸;三四区长,民多怨言。村公所老百姓常称之为最高权府,村长多由各董事指派,县府加委。此辈多系豪劣,一字不识,理政无方。区府派款一百,村长以二百收,闾长以三云。
教育之幼稚
临河教育幼稚,人材绝无,事属真确。学校虽多,但多办理不善。县立一校,历史较长,毕业学生仅二十余名,升入中学校者,十余名,中途辍学者六七名。县立女校,创办有年,迄未举办毕业,各区小学校共二十所,师资多下架商人,或村公所计帐先生。学生以住家很远(按:一村大至三四十里,而住户零散其间),就学者无几,今春开办者仅九处。现一四两区校长,闻系邮差夫与高小毕业生,县立一校之教员,多系落伍军人与“混饭者”辈,学生原有一百二十余名,现仅十几人,传称教育局长系一初中一年级肆业生,督学乃一办垦污吏,无怪各校现状之糟粕也!
民生与党务
临河自设治以来,平均年年有灾,非兵即匪、水、雹,民间之苦远甚于其他各县。去岁王军屯庄供应繁重,出自佃户,地主、村闾邻长多从中渔利,村成废土,民多流亡。临河位于绥西,交通不便,素无党人足迹。民十九春,阎冯之变,北方党务停顿,始有党员潜往。二十年党务公开,省部派高建章氏为人民团体指导员,组织人民团体。入夏改派筹备员筹备党务,九月正式分部成立,当时共有党员七人,后增至二十人,刻此土劣嚣张,负责人多离境云。
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就送梧桐子“ ”支持吧!
”支持吧!
已获得0个“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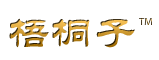
 河南省孟州市
河南省孟州市 山东省新泰市
山东省新泰市 广州市海珠区
广州市海珠区 安阳市 北关区
安阳市 北关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