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故事---隆尧一中人物忆旧(他人回忆)2
家乡区县: 邢台市隆尧县
1964年夏天,学校在文庙北面四十米开外,新建成一排教师宿舍。我住东数第三间,他住第四间。成了邻居,这才有了第一次对话,不过打个招呼而已。一中奇人、终生未尽其才、河北科大教授叶庆刚在隆尧
叶庆刚老师绝对是隆尧一中最有特色的一个人。他把自己封闭起来,除了工作关系,他几乎不同任何人来往。我们倆曾住同排宿舍,比邻而居,天天见面,四年间对话时间的总和超不过一小时。我到一中后一两个月内,全校50多名任课老师,几乎都认识了模样并且打过招呼。唯独与叶庆刚老师认识最晚,也从没有打过任何交道。他独来独往,“特立独行”。别人已经告诉了我他的名字,说他是从北京下放来的,教高中物理,业务很棒,使我一开始就有好感。他住的那个屋我知道,经常从他门前路过,却从来没有进去过;有时走个碰头,我迎上去想表示问候,他却目不斜视,低头而过,“旁若无人”。这种情况一直保持了一年有余。
后来有人告诉我,他有海外关系,解放前的清华大学毕业,属于旧知识分子;解放后又历经过多次政治运动,1958年,被从外贸部下放到隆尧,思想有负担,生怕一不小心犯了错误,再遭不幸,所以整天谨小慎微,自我封闭,以为防范。难怪他在所有的全体会议上从不发言。平时每周一次例行的政治学习,如学“修养”、学“九评”,他在理科组是否发言,我不知道;后来的“思想革命化”、“四清”、“文化大革命”等集中学习,好多人抢着发言以表示“积极”的时候,他也是把凳子放到最偏远最不引人注意的角落里,坐在那里洗耳恭听,即使几个小时,也从不走动,却始终一语不发。
住成邻居,我发现他许多“不近人情”的地方:他的宿舍基本上不让别人入内,学生交作业,他只开半扇门,接过本子马上关住;他也从来不到别人屋里串门,即使是同时从隆尧二中调来的田文秀,又同住在这一排,二人说话也只在房门口,互不进屋。“四清”后期,他爱人带两个女儿来到一中,四口人挤住在这一间十平方米左右的宿舍里,绝对见不到她们出屋活动。他的大女儿下学回家,背着书包一路低头快走,闪进屋内,马上关门,在夏天也不例外。他的小女儿憋得难受,经常站在后窗台上遥望屋后那堆满烂砖的荒园和远处的土城墙。每逢看见有人走过,就赶紧缩下身去,生怕被人发现。即使如此,他也不放孩子们到室外玩耍。我当时很不理解他竟害怕到如此程度,为这两个孩子可怜的童年深感不平。在他感到如此严酷的环境中,他把一切精力都投到了工作上和劳动中。除去上课以外,不见他有任何业余爱好或休息方式,唯见他整天憋在屋里学习看书,钻研业务。
叶老师特别勤奋,无论冬夏,他熄灯最晚。大热天也从不在门口乘凉,当我和同排住的赵惠田、张世荣等同龄人,夏日晚饭之后,在屋门前的小院中,坐着小板凳,古往今来,天南地北,海阔天空,神聊说笑时,他正趴在办公桌上又写又读。那时既没有电扇,更没有空调,他就那样赤膊短裤汗流浃背地坚持着;偶尔站到门口,伸伸腰肢,遥望夜空,深吸几口新鲜空气,就是最好的休息了。地震以后,为安全起见,全校师生都让搬到苇席搭建的简易棚中睡觉。他在哪里就寝我不知道,但他不怕余震危险,每天晚上照旧回屋开着灯看书写字,一熬半夜,是我经常见到的。
他特别勤劳。冬天夜里下了雪,我们还没有起床,他已经把那一排所有人门前的雪都扫净了。春夏天晚饭前,他至少要劳动一小时,从饭厅前的洗碗池那里接水,用脸盆端到文庙后那一片,浇园地中及其周边的几十棵小树,上岗下坡,往返一次不下百米,每天不少于几十趟。秋天他又扫门前的落叶或者继续端水泼院子。
他尽管力图摆脱旧社会带给他的影响,努力改造自己,但几十年的耳濡目染,一些习惯动作会下意识地表现出来,比如他偶尔当众说话,会不自觉地双肩一耸,两手向外一摊,摇一摇头,表示无可奈何。这种肢体语言那时在乡下独一无二,只有在电影中才能见到,这欧美人的做派,就暴露出了他是接受过西方现代教育从城里来的知识分子。他虽然教物理,却对杠杆原理运用不好。一次劳动,他用桶担水,前边桶小,后边桶大,他缺少实践经验,照常把扁担中点放到肩上,这自然会后沉,他不调整支点和力臂,却使劲用双手压住扁担前段,力求平衡,还走不稳当。那种拙笨费力的样子,引起初一不少小孩子驻足观看。他们哪里知道,这个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原本就不是以担水为其特长的啊!
叶老师也有他幽默风趣的一面,不过这只在他信得过的人面前偶尔表露一下。1966年10月中旬以后,由外地传来要批判工作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一时间校内学生组织先后成立,“官办文革会”失去了作用。学生纷纷外出“串连”。革委会时代揪出的“重点人”虽未宣布“解放”,实际上已没有人顾得上管。胆子小的呆在家里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自己觉得没问题的,也就跟“革命师生”一起外出串连或参与其他活动,事实上已经“平反”。学生组织“勒令”工作组检查“煽动群众斗群众”鼓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错误。工作组正组长姜星杰当天夜里带上行李不辞而别,只剩下副组长贾锦章来接受“革命小将”的批判。有一天,邓联璧老师对我说:“叶老师也会说笑话,他问我:‘你看老贾紧张吗?我看他不是真紧张,他是假紧张(贾锦章)。’”这使我两个都笑了。此类情况恐怕是绝无仅有。更多情况下他是循规蹈矩,谨言慎行,不敢越雷池半步。
尽管他处处小心谨慎,却仍然摆脱不了挨整的命运。“文革”开始不久,他就成了“重点人”,曾与其他十几名“牛鬼蛇神”一起,“登台亮相,自报家门”,即在工作组和“校革委”主持下,在舞台上排着队,面对台下800多名师生,逐一报出自己的姓名和所犯的错误或“罪行”。轮到他时,只见他左臂腋下夹着一块写有他的姓名上面打了大黑叉子的硬纸牌子,站在舞台中央,立正了规规矩矩地说:“叶庆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说的什么记不得了。当时也看不出他有特别的紧张,他的做派就像大学教授拿着讲义去给学生上课。由于他讲课好,工作认真,在学生中威望高,工作组一走,他便获得了一年多的自由。到了1968年夏岁月匆匆,一晃四十多年过去。天“清理阶级队伍”时,他又难逃一劫,再次成了“重点人”。我们住在西甫小学搞运动,没有见他来过。岁月匆匆,一晃四十多年过去辗转询问,联系上了在河北科技大学工作的隆尧一中初中45班毕业生尹升方,他在电话中告诉我说,叶老师已于2008年1月18日病逝于省三院,他曾去帮助处理后事,消息绝对准确。我与宋校长知道后,相对感慨了许久。。
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就送梧桐子“ ”支持吧!
”支持吧!
已获得0个“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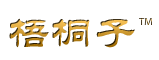
 河南省孟州市
河南省孟州市 山东省新泰市
山东省新泰市 广州市海珠区
广州市海珠区 安阳市 北关区
安阳市 北关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