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闹房》
家乡区县: 山西省闻喜县
众人不知,就有人追问,也有人说:“在他爹娘屋里呗。” “嘁,谁家十七、八的大闺女跟她爹娘睡一个屋,那还不碍她爹娘的事。对了,俺给伙计们说个笑话,说是城里有一家卖肉的姓张,俩口带一个十七、八的大闺女过日子,城里地方窄狭,实在没办法分屋住,闺女大了,再不能一炕住,就在大炕边给闺女支了张小炕。晚上,两口办事,摸摸索索、哼哼唧唧的,把闺女惊动了。迷迷糊糊问:“娘,啥动静?”她娘说:“老鼠要进洞。”闺女大了爱操心,就说:“看把肉咬了。”就要摸索着点灯起来看看,她爹急了,就慅气说:“睡恁觉,做恁梦,管毬进洞不进洞。”闺女说:“老鼠偷吃呢。”她爹更气了,说:“做恁梦,挺恁尸,管毬偷吃不偷吃。” 笑话说到这里,碳脚子们笑成了一堆,先睡觉的也没了睡意,七嘴八舌抖着荤料子。那客人又说:“东头两间,一明一暗,掌柜的老两口睡在尽东头暗间,明间靠西墙是小姐的铺,跟那位后生只隔一层墙,知道这山里隔墙拿啥做的么,是用荆条编成笆子,两面各涂上一层泥,时间一长,泥裂了缝,两边就透了亮,放个屁对面都能听见,要是运气好,还能瞅见点啥。” 长山正整理衣被准备睡觉,听了这话赶紧爬在板壁上看,另有几位也往跟前凑,那位客人就噗嗤笑了。说:“恁这后生倒是猴急,那一家子还在东厢伙房里收拾呢。”长山有点尴尬,好在灯影里也看不见,就讪讪地坐在铺上脱衣睡觉,那几位也退回去休息。 有人熄了马灯,屋里暗下来,小得和大得已响起了鼾声。长山睡不着,他躺在铺上假寐,那丝隐隐的期待烧灼着他的神经,他心里象装了火球,脸上滚烫,手脚激动得微微颤抖,全身的知觉都集中在耳朵上,仔细地谛听着东厢饭堂和院里的动静。 锅碗瓢盆的叮铛声告一段落之后,他听到饭堂的锁门声,在意识里,他把这些声音转换成了画面:白鲜跟她娘先提着灯出了饭堂往茅房去,提了尿盆回北屋整理床铺睡觉,掌柜和伙计到院里,先去马厩添了草,掌柜嘱咐伙计别忘添夜草,伙计在马厩插门睡觉。掌柜摘下院里的马灯,提着去了茅房,撒尿,咳嗽,又到客房来转了一圈,看到煤客们都已酣睡,才带上门回隔壁主房去了。 白鲜和她娘正在里屋有一句没一句的拉着闲话,掌柜进屋,白鲜就到外屋拾掇睡觉,长山听到窸窸窣窣脱鞋、扫炕、铺被窝、脱衣服的声音,激动地喘不上气来,他侧脸朝墙,急切地搜索,希望能找到一条缝隙或一个小孔。居然找到一个,孔里漏过微弱的光,长山赶紧把眼睛贴上去,只能看到里屋亮着灯光,外屋黑洞洞的,啥也看不见。
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就送梧桐子“ ”支持吧!
”支持吧!
已获得0个“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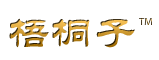
 河南省孟州市
河南省孟州市 山东省新泰市
山东省新泰市 广州市海珠区
广州市海珠区 安阳市 北关区
安阳市 北关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