梧桐落,又还寂寞
庭院静好,岁月无惊。
秋风渐起,窗外的梧桐叶在半空中瑟瑟地飞舞着、、、、、
一片又一片,竟落了满满一庭院。
她端了茶,轻轻推开那扇半掩的门,踱步而入。只见他一袭青衣,负手立于窗前。久久地,凝视着窗外那颗苍老的梧桐,一动也未动,甚至连她走进来也未发觉。
风已然飘了进来,吹得书案上的宣纸瑟瑟作响。纸上字迹隽永,墨迹未干。
银床淅沥青梧老,
屧粉秋蛩扫。
采香行处蹙连钱,
拾得翠翘何恨不能言。
回廊一寸相思地,
落月成孤倚。
背灯和月就花阴,
已是十年踪迹十年心。
她默默放下茶具,抬头望了一眼疏窗前那道背影,孑然凄立。
十年了,他终是忘不了她。
他的绝色表妹,那个站在阳光里,黑发如丝缎,对他微笑的女子。他一直以为,她可以 嫁给他的,却不想,选进宫,成了皇帝的爱妃。
少年时的绚美如蝶的梦,翩然而落。
只是这些,是嫁他之后才渐渐知晓。信手拾起椅上的长袍,慢慢靠近,覆在他单薄的肩上,微语,天冷,添衣才是。
他一怔,微微侧头,手亦覆了上来,了然一笑。
似三春水,暖意绵绵。他与她,如今这般,能举案齐眉,已算幸事。
犹记初嫁他时,他是相国公子,丰神俊逸。她是贵府千金,朱颜玉貌。真真一对璧人,羡煞旁人。她也以为,从此可以神仙眷侣。
可她发现,他不快活,一点都不快活。纵然他是相国公子,满腹才情,那又如何,他还是活得那样愁苦。终日郁郁寡欢,借酒浇愁。她不能懂。一点也不能。
幼抱才捷,仕途虽平顺,却不大受重用,恐怕他也心知肚明——自己这御前侍卫的荣衔只不过是皇帝御前的摆设。明是用来安抚功臣之心,暗地里却是用来阻止他明珠父子权势进一步扩张。八岁登基,深谙帝王心术的康熙怎么会放心放他去六部历练呢?对他纳兰容若,明是亲近,暗藏挟制。任他有“经济之才,堂购之志”,也只得匍匐于皇权之下,身不由己地皇帝和自己父亲政治较量的牺牲品。
这男子,处处皆是苦,苦的让人心疼。
那年春日,他在轩下醉得醺然,恍惚中看见她走来,眉目婉约的脸,走过来帮他把被子掖合。他于微醉中静静看她,默默感动,这女子,静得如此端然,自打嫁进府邸,竭尽心力,却从不多问。竟不觉地自身眼角眉梢情意在细长拖延。
自那日,他才看到,这眼前的人儿,亦对自己情深意重,何尝不苦呢?
才恍然顿悟:满目山河空念远,不如惜取眼前人。
自此,琴瑟相和,红袖添香。
兴致正浓时,他亦会着手教她临摹,伴她读书,嬉笑逐闹,声声笑语,穿透回廊。
他们戏将莲菂抛池里,种出莲花是并头。
他们被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
他们忆得双文胧月下,小楼前后捉迷藏。
他们更把纤眉临镜画,梧桐花下誓三生。
一次大雨,他在书房看书,久久不见她来,便急急去寻,四处遍寻不着,突然看见她在后院撑着两把伞,一把遮自己,一把遮着刚开好的荷花。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人间最美,也不过如此。
梧桐花又开,三载匆匆而过。
产房里传出她凄厉的叫声,声声揪扯着他的心。他在房外,焦急万分。
声音终于渐渐平息,他破门而入,看到的,竟是她惨白的面容、、、、
他不信,这一定不是真的。她才十九岁,如花绽放的年纪,怎么可能?这个噩耗太突然、太残酷、太无情,他不要相信,她就这样撒手人寰。
他不要。
、、、、、、、
又是一年。秋色正浓。
他站在这里,立在残阳疏窗之下,看见落叶萧萧,是西风有来过,轻轻翻动心底片片往事,骤然间,想起那么多与她生活的枝蔓,
她浅笑的脸,新阳熠熠,一如她的人温暖和煦。
他似乎隐约能看见她的逆光侧脸、睫羽,和脸上细微的痣。还有笑起来时,眼角细小的纹。
一切这样清楚,才深知,原来他爱她,已深入骨髓。
谁念西风独自凉,
萧萧黄叶闭疏窗。
沉思往事立残阳。
被酒莫惊春睡重,
赌书消得泼茶香。
当时只道是寻常。
呵,原来要等到失去以后,才会明白那销魂蚀骨的寻常。
如今,她已然魂归香丘。
踏着这纷纷落叶,微微仰着,伸手触及,这梧桐叶,是她寄给他的相思么?
梧桐相待老。
原来,自己一无所有。
叶已落,又还秋色,又还寂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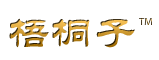
 大同市 城区
大同市 城区 茂名市茂南区
茂名市茂南区 龙岩新罗区
龙岩新罗区 河北省沧县
河北省沧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