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的湮灭
断开的头颅在池子里静静的惨白,从紧合双目的那张脸上看不到窒息之前的容颜,头顶的水哗哗的奔涌而下,因为收缩而短下去的一节表皮露出底下的骨肉,把其中沁出的血渍稀释淡化。微微飘出甜腻的水迅速注满了水池,欢腾的奔向池底的注水口,淡淡的殷红转瞬不见,凌乱的发丝在水中轻轻浮起。
每一个花谢的瞬间都有一个灵魂湮灭,每一个灵魂湮灭的间隙都有一颗心肝肠寸断。
赤河冷漠的淌过这个冬日的华年,失去焦点的视线再也汇集不了情感。
倒挂的断颈滴落颗颗透明的液体,不会蒸腾亦末凝结,应声落地,融化开来,也留不下水痕,原来身体里流过的是这样淡漠。
可悲的人总是哭喊着离开,挣扎着走远,然后无可奈何的原谅并怀念。回到原地才发现,徒余一地颓靡,尤现一面苍白。
那些透明的液体从断颈一样可悲的眼睑滑下,不会蒸腾亦未凝结,应声落地,融化开来,留不下水痕,其实身体里流过的一直这样淡漠。
黑暗像潮汐一样袭来,习惯了夜的存在所以一如既往的前行,昏黄的灯光突然在楼道里绽开,足之顿处,惊恐了瞬间。
抬首间,咝,倒吸一口冷气,那颗头颅凭空而现,黑红色的血液从顶心放射而下,模糊了面。合上双目,加快了步伐,迎上那个个血淋淋的东西,啪,影像如同星光散开,眼前,昏黄已灭,夜色正凉。
茫然四顾,芳华正好,岂感淡漠,一场梦而已,孩子,洗洗睡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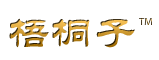
 大同市 城区
大同市 城区 茂名市茂南区
茂名市茂南区 龙岩新罗区
龙岩新罗区 河北省沧县
河北省沧县